《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
作者 | 艾哈迈德·萨达维
我想以一句《共产党宣言》的戏仿作为本文的开头:“一个幽灵,一个复仇者的幽灵,在巴格达的废墟上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警察和记者,美军与狂信徒,都联合起来了。”这是我能想到对《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一书最简明直接的阐释。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作者为艾哈迈德·萨达维,伊拉克小说家、诗人、编剧,1973年出生在巴格达,曾做过纪录片导演,著有诗集及3本小说。萨达维的作品多次获奖,2010年,他作为40岁以下最优秀的阿拉伯作家之一,入选“贝鲁特39”(Beirut39)。凭借《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一书,萨达维成为第一个赢得I.P.A.F.(阿拉伯国际小说奖,阿拉伯国家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的伊拉克作家,他的同胞和其他阿拉伯作家将这次获奖看作巴格达的“复苏”。
Part.1
“今天的现实富得像是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颗鹅卵石。”阎连科这个略显悲伤的论断道出了今日写作者们最大的困局。
尽管现实的确像是一座矿,但最外层的富矿早已在二十世纪之前被开采得所剩无几。新的现实埋藏在这座矿山的更深处,而我们还在试图找到一条通向它们的缝隙。这并不容易,因为越是向下开掘,旧的经验便越是难以胜任。
艾哈迈德·萨达维的写作无意间呼应了这个问题。2003年,美军对巴格达内萨达姆可能藏身的地点进行了猛烈轰炸,无数建筑被炸成废墟,平民死难者更不计其数。2005年,美军接管巴格达。基督教徒伊利希娃老太太独居在巴格达,而死亡就与她比邻而居。死亡发生在人行道上,发生在酒店门口,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艾哈迈德的任务是发现,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文学,究竟该如何完成对全新的现实的书写。
在巴格达生活,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习惯死亡的存在,把它视为亲密的睦邻。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让死亡科学化、精细化(“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保罗·策兰),逼迫人们(譬如乔治·斯坦纳)一再追问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何存;而恐怖袭击则让非自然死亡如同病菌一样侵入生活,最终让死亡变得日常化。
这意味着死亡的悲剧性不仅被消解了,甚至还成为某种苦中作乐的素材。
伊利希娃老太太的邻居,一个孤独的拾荒者哈迪,收集了死于人体炸弹的死难者的碎尸,并把它们拼合在一起。这大概是出于纯粹的无聊,因为哈迪并不是一个富于黑色幽默的艺术家,也并非一个用琉特琴对抗强权的勇敢流浪诗人。他最大的愿望无非是用奇闻轶事在酒馆里抓住听众的心,这是像他这样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
一条死于恐怖袭击的冤魂急于找到可以用来栖身的尸体,于是它钻进了哈迪的杰作中,并把它唤醒。于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诞生了一个新时代的弗兰肯斯坦。
Part.2
作为小说而言,《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的结构无疑是松散的。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傀儡般登台又退场,各自的故事迅速地交错,又立刻各奔东西。
这使得小说本身,或者说,整个巴格达,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弗兰肯斯坦,向读者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将尸块缝合的粗陋针脚。
理解艾哈迈德的缝合术更为重要。在这里,拼贴的形式重要性远大于内容。但这里并没有波普艺术的轻佻。围绕着无名氏,挣扎求存的拾荒者,充满野心的记者,利用超自然顾问追捕无名氏的准将,这群人的行动在阿帕契直升机的阵阵轰鸣声中汇聚成了一支不甚和谐的交响曲。
艾哈迈德笔下的“无名氏”同样取材于随处可见的血肉碎块,同样有着不死之身与一身蛮力,但它已经迥异于他的先祖。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在本书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借喻。与前者反复强调的人性相比,后者几乎是在以最大限度剥离其人性。无名氏放弃了喋喋不休的追问——“我是谁?”“为什么制造我?”“我该去哪儿?”;在短暂的失落与彷徨之中,他迅速找到了自己需要成为的目标:一个复仇者,复仇天使。
他的确扮作伊利希娃老太太早已死于恐袭的儿子,在她家中陪她坐了好一会儿。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组成无名氏的每一个部件都不想重新获得人类社会的接纳——它们都在以腐烂相威胁,逼无名氏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永无止境的复仇行动。
不复仇还能回到哪里呢?在巴格达,尸体甚至没有坟墓。已经不可能回到生前的那个社会中了,因为正是那里让他们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碎尸。
被人的碎块拼合而成的弗兰肯斯坦变得比任何一个独立的人都要单纯。为了让这个庞大的躯体能够像人一样行动,这个躯体中只保留了一个理念,那便是向暴力复仇,而复仇同样需要暴力的介入。
一个悖论出现在他的复仇之路上:每用暴力消灭一个施暴者,无名氏身上的一块肉便会因为心愿已了而迅速腐坏。这使得他不得不去寻找更多受害者,用他们的肉来维系自己身体的完整。但当受害者也不够用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那些施暴的人。到最后,善恶的边界也在这里被模糊了。
伊恩·麦克尤恩认为,在小说中注入科幻元素,是为了指向现在,而非指向未来;而对于无名氏来说,当他走上自己的复仇之路时,他已经深陷加害——复仇的死循环,不会再有什么未来了。
Part.3
经由不断的再发现与再书写,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已经成为了一种想象科幻的符号。
她所创造的那个由血肉碎块拼贴起来的怪物是一个造物,而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人——如果他的父亲,弗兰肯斯坦博士,愿意接纳他的话。他需要一个类似于洗礼的命名仪式,但最终没有得到。他由此而成为一个游荡在人与造物罅隙之间的幽灵。
在不断的再创作过程中,拼贴永远是一种想象弗兰肯斯坦的最重要的方式,同时也是理解弗兰肯斯坦意象的武器。无论是在电影或是动画作品中,弗兰肯斯坦的标志都是盘亘在脸上的,粗大如蜈蚣的针脚。
要想理解这个怪物的真面目,就不得不理解它是如何被拼合的,并沿着拙劣的缝线将它重新拆开。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是因为拼贴是一个无论在东西方语境下都能迅速得到理解的概念。比如在中国,每当一名婴儿降生,民间有收集左邻右舍家中的布条为新生儿制作百衲被的传统。与日本的插花不同,在制作百衲被的过程中,拼贴这一行为被反复强调。它的人造属性、非自然属性正是它的力量之源。
一方面,拼贴象征着群体的力量;另一方面,拼贴的非自然也带来了恐惧与不安。在当代,拼贴也可以如徐冰的《凤凰》——“凤凰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凤凰》,欧阳江河),直指我们的焦虑。它宣告了在新千年,郭沫若式的对凤凰的想象已经破产。
徐冰的拼贴术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它用庞大而包容的凤凰之理容纳了数以吨计的电子、建筑垃圾。但从上古活到当代的始终是作为骨架的理念,或者说,除了理念之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一切都不再相同。
这或许可以为我们该如何理解弗兰肯斯坦这一意象提供参考。弗兰肯斯坦的出生注定是一个悲剧。其一,这个庞大的活跳尸诞生于从坟墓中盗掘的尸块,这象征着宗教意味上的不洁:它的诞生本身便象征着以暴力手段破坏神圣的生死界限。这种隐忧早在俄尔普斯的悲剧中便得到书写——试图将爱妻从阴间召回的音乐家,最终死于狂女们的手中。
其二,由无数的尸块拼合这一过程,则象征着其身份上的含混,以及“自我”边界的模糊。如小说中所言:“快去找你的遗体……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他们彼此呼唤着对方”(p33-p39);身份的混淆与缺失最终导致他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一样,不得不走上放逐之路。
其三,电气刺激所赋予的灵魂,则暗示了对上帝造人手段的卑劣模仿,而这便直接将弗兰肯斯坦推到了上帝的反面。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与其说来自于被自身造物主的抛弃,不如说是命中注定。
Part.4
弗兰肯斯坦的生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减退。在玛丽·雪莱的小说结尾,造物者和被造者一齐掉入大海,同归于尽;但造物者死了,被造者却爬了出来,仍旧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取了同样的结尾。政府抓不到无名氏,最终只得草率地抓住拾荒者哈迪,把所有的罪行都扣在他的头上。在无名氏诞生的那条老街上,该走的人走了,只剩下无名氏和被伊利希娃老太太遗弃的猫。在小说的结尾,旧的演员悉数退场,而无名氏自己仍旧站在巴格达的土地上,等待着下一次开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哈迈德·萨达维用自己的家乡作为素材,完美地完成了一次弗兰肯斯坦故事的当代续写。
理解了无名氏身上的针脚,也就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暴力,以及孕育暴力的土壤。让几十个不同的意志坚定地合而为一的,正是对以暴制暴信条的绝对信赖。
巴格达之于无名氏,就像大地之于巨人安泰。它完美地回答了开篇之中阎连科的问题——对于现实的富矿,如果找不到足够新的工具,就再回到旧的工具箱里找找。
注:为便于表达,文中用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字直接指代玛丽·雪莱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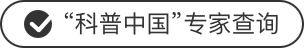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