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又一次回想起妻子去世一周前的那个晚上。
那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提前订好靠窗席位的法餐厅,她从人类基因组研究院的实验室过来只需要十分钟的地理位置。我希望这是一个我们会永远铭记的美好夜晚。
她出现在店门口时,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我注意到她脸上掩饰不住的疲惫,知道她一定又一心投入实验忘记了时间,终究忍不住说:“慈,你其实不用老是这样为难自己。你是遗传学专家,还成为了早衰综合征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没有几个人26岁能做到这样的地步。”
她笑了笑,说:“你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看着她脸上云淡风轻的表情,心中酸涩:“我很担心你。你知道,最近有一批涉足基因编辑领域的专家突然死亡,其中就有我们生物信息所的同僚。官方的调查结果是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但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说不定是那些激进的伦理主义者有组织的攻击。你们的研究也并不安全。”
她像安抚一样拉住我的手,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枝鹰,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和想做的事,我很满足。我唯一的遗憾或许就是没能和你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不管未来如何,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她凑近了一些,说出了那三个字。
我怔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亲口对我说过这句话。
那晚她脸上的笑容在灯光下显得分外虚幻。
妻子死于早衰综合征带来的器官衰竭。医生早在二十年前就对她下了断语,九成的该症患者的生命都将以这种方式结束,在30岁来临前的某一天。
也许在那个夜晚,她已经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预感。
尽管早已做过心理准备,但是一开始否认和愤怒的狂潮还是席卷了我。得知她死讯的一周来,我没有去生物信息所上班,一味把自己关在家里。家里她的气息还没有消散,她的DNA分布在每一件我能触摸的器物上,宋慈好像并没有离去,到了明天,又会打开家门,说自己只是不小心又在实验室通宵了一晚。
在这个遗传学高速发展的年代,从基因层面根治遗传病已经成为可能。宋慈,五岁确诊早衰综合征,十六岁决定自救报考生物学专业,二十三岁协助导师团队找出了早衰症的病因,确定了基因上两对突变的致病碱基的位置,现在又通过基因编辑成功治疗小鼠早衰症。也许只要再有十年,甚至是五年,她就能够战胜早衰症,我们就可以一起从容走到生命的尽头。
现实总是这样荒诞,就像基因中一个偶然的、小小的突变竟能决定两个人的一生。
突然间玄关传来了敲门声。
走开,我想说,但是嗓子干涩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从地上爬起来,打开房门,声音哑涩:“别来烦我。”
“吴先生,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心情听人讲话。但是事关杀害您妻子的凶手……”
“你说什么?”我抬起头来,几乎扑到来人身上。
“是的,您的妻子并非是自然死亡,我们已经抓捕了凶手。”
这时我才看清楚他的样子,他身着便装,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警察。
“这是怎么回事?凶手在哪里?”
“您跟我来,我们会把一切如实告诉您。”他做出邀请的姿势。我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正常,但是我必须弄清宋慈死亡的真相,我没有第二个选择。“带我去。”我说。
车子拐进了江边的一个小院,它在这个安宁的、行人往来的街道上毫不起眼。
男子领我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女性鞠了个躬后就离开了。那名女性放下手中的材料,说:“请坐,吴枝鹰博士,我们说来话长。”
我依言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我是这次科研人员连环死亡事件调查组的组长,你可以叫我肖焰。开门见山地说,您的妻子宋慈博士也属于本次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多名受害者之一。”
“到底是谁伤害了她?”我急不可耐。
“我相信您已经知道了最近两个月内发生了多起生物技术专家的离奇死亡事件,受害者的死因,通过正常的医学手段,只能够检查出免疫系统崩溃和急性器官衰竭。我们的研究员起初认为这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病的表现相似,认为可能存在某一类的核泄露事故。但是经过对这些受害者尸体的进一步检测,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其一,这些尸体不存在任何辐射,其二,核辐射只能够破坏染色体,将其像积木一样打散,但没有办法将积木全盘端走。但是这次受害者的身体中,没有留下任何DNA物质,从脊髓细胞、骨骼细胞到手指上的皮肤细胞,没有一个细胞中能检测到DNA。”
“这不可能,千万年前的人类骨骼中尚且会留下DNA片段。”我背脊一阵发寒。
“事实如此。尽管我们也无法相信,但是在一瞬间,所有DNA物质从受害者身体内被移除。”她接着说,“我们追查到了一个名叫‘除草人’的组织。正是他们通过某种手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我们抓捕了他们的领头者和部分成员,宋慈博士是他们的最后一个目标。没能救下宋慈,我们很抱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脸煞白,能做的只有提问。
肖焰示意我不要激动,开始在她身侧的屏幕上播放一段视频:“你先看领头者的这段审讯视频。”
屏幕上只有一个人的身影,我认出他正是国际遗传学学会的会长马尔特,我和宋慈曾经在几次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和他打过照面,一个平易近人的有趣老头,这是我当时对他的印象。但是此刻他的神情高傲而诡谲,全然不像我认识的那个马尔特。
“‘除草人’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画面外一个男声这样提问,我意识到这是调查组的审讯员。
马尔特说:“别着急,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在大草原上住着一户人家,他们以游牧为生。虽然他们的羊很小,但是他们非常勤劳,将羊群从一片草地赶向另一片草地,相信羊终究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牧羊人随身携带着牧草的草籽,经过荒芜的土地时,他们就会从携带的布包里掏出一把来洒在地上,期盼下次再见到时,这里会变成一片丰沃的草场。
“第二年春天,牧羊人回到了那片曾经荒芜的土地,这里果然长起了牧草,他们感谢着上天的恩赐,然后每年计算着草最为茂密多汁的时候,准时赶来他们的羊群。年复一年,羊渐渐长大。但是好景不长,那片草地生出了杂草,杂草会使优良的牧草变得缺乏营养。羊吃不到好草就无法成长,于是牧羊人找来了除草人,让他们除去杂草、保持草地的丰沃……”
“听起来像是一群极端的自然主义者,想要通过封锁基因编辑技术来保证人类基因的纯净。”
马尔特大笑起来:“特工先生,您的意识是多么以人类为中心啊!那么您能告诉我人类是什么吗?是您的身体,眼睛、鼻子、耳朵这些感官,还是生物学上乏味的描述性定义,又或者是您宝贵的心智,您的情感、您的理智呢?——一直以来人类都是以此和那些‘低等的动物’划开界线。”他的表情变得严肃,声音逐渐高昂,“您看不出,人类也不过是基因制造的一种生存机器罢了,和这个地球上千千万万种的生存机器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切都是复制因子40亿年的漫长旅程。从原始海洋中开始,在改造它的机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创造了复杂细胞、创造了有性生殖、创造了肌肉纤维、创造了视觉,接着创造了情感和意识,在这里说话的你我,然后最终以死亡统扩了一切。那些生存机器,肉体和心灵,没有以任何方式留存下来,唯一长存的只有基因,它保留了亿万年旅途的所有痕迹,在堆积如山的机器残骸上接着建造新的机器。只有基因才是所有生命的本质。”
“既然基因如此宝贵,你们为什么要破坏被害人的基因?”
马尔特因为刚刚的一段演讲感到疲累,靠在椅背上,如同没有听到他的问题一般,说:“耐心一点,让我把那个被你打断的故事解释给你听。
“荒芜的草地其实是一颗荒芜的星球,此时距离它的形成才仅仅过去了5亿年。在它的表面除了一片没有生机的大海、大气中的简单化合物和放电反应之外别无他物。‘牧羊人’在巡游中发现并考察了这颗星球,洒下了一把‘草种’——碳基的复制因子。这时的‘牧羊人’文明已经在一个文明层次上停滞了数十亿年之久,为了突破科学瓶颈,‘基因放牧’作为诸多的突破方案之一被提了出来。‘基因放牧’不同于那些检视学科基础的方案,它直接质问‘牧羊人’作为一个有限物种的意识能够认识的概念装置的局限性,并且认为要突破严密的科学壁障,只有突破有限的物种意识这一个办法。
“‘牧羊人’的生物演化之路,和人类一样,越过了无数阶梯,但最终停滞在了‘意识’这个阶梯之上。他们发现所有‘意识’的机械造物并不能够真正地跨越‘意识’的局限,所以为了跨越这个阶梯,他们建造了一个堡垒级计算机、上面搭载了‘牧羊人’文明中最高级的人工智能,足以同时处理数个星球的遗传物质数据和数亿年的环境数据,它就是故事中的‘羊’。在‘牧羊人’准备的广阔草原之中,地球只不过是一个一米见方的草地。‘基因放牧’的终极目的,就是对所有播种星球上的遗传物质演化和环境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预测,从生命无限的演化可能性种找出一条道路,由此创造出一种新人,不,一个新的物种,一种新的生命……”
他的眼神狂热了起来,“特工先生,难道您从来没有过超越自我意识的冲动吗?如果走上这个阶梯,那么这个生命能够摆脱所有次级的认识途径,超越一切名词和单个实体,而能直面宇宙的终极真理,他将认识和理解第一推动,他将成为道。与之相比,人类的心智、人类的意识就只是一条扭曲的、幽暗而又泥泞的小路!为了他的即将到来,我能做所有事,可我只能做一个清除污染数据者的、微不足道的除草工!”
“你们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被跨国行动组捕获,你可以在监狱里和他们分享你的狂想。”
马尔特又一次大笑了起来,“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疯子。五年之后,‘羊’就会造访地球。那时地球上所有的遗传物质都会成为‘羊’的养料。这对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哪怕是像您这样缺乏领悟力的生物,多么美妙的福音!”
马尔特尖厉的话音戛然而止,肖焰关掉了视频。他夸张的神情和疯狂的话语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无法想象这人曾经是一个理智的科学家。
肖焰也没有说话,室内异常地沉默。
过了很久,我艰难地开口:“难以置信。就因为这样疯狂的想法……”
“可惜这不是狂想。你看看这个。”她拿出了一个白色长方体放在桌上。
一眼看过去,就像是家用电器的遥控器,只是上面没有按键,而且表面出奇地光滑,也看不出任何缝隙和使用痕迹。
“他们叫它‘镰刀’。我们把它送到了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和武器实验室,从结论上来说,这绝不是人类文明现在的科技水平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存的手段能够破坏或者侵蚀它,也没有办法打开它的外壳、进入它的内部结构;即使使用了最先进的慢速侦测技术,我们也只能观测到在触发之后,目标体内的DNA在最小观测时间中凭空消失,其间没有放出任何形式的射线或者是空间扭曲。我们知道的唯一一点就是它的目的不是一个破坏装置而是一个收集器——针对不同的生物个体,‘镰刀’本身触发后的增重与个体体内DNA总重接近。这就是我们目前获得的所有信息。”
“你是说,马尔特说的都是真的。”我说。
“我们不得不考虑他的话真实的可能性。”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把你叫到这里,是因为你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遗传学家,我想请你从生物学的角度寻找一种方法,从这把‘镰刀’的手上保护人类的DNA——如果‘羊’真的会到来的话。还有其他不同领域的专家也在合作寻找抵御之法。考虑到反对组织还没有完全清除,存在着各种风险,所以如果你拒绝……”
“我接受。”妻子的死让我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然后我按她的指示拿起了那个白色物体,它的重量超出了我的预料,我的眼眶有些酸涩:“宋慈的DNA也在里面吗?”
“不。那时核心成员已被拘捕,你的妻子死于外围成员的投毒。”
“镰刀”的研究让人一筹莫展。肖焰秘密地在生物信息所里给我搭建了一个班子,并且以其他研究项目的名义制造了一个幌子,可以优先使用一切资源。但是三个月来不断的试验只是让我用‘镰刀’收割了更多小鼠、大鼠、斑马鱼、转基因植物和微生物。我弄清楚的唯一信息是高度碎片化的基因信息不会被收集和读取,但到了基因断裂到了那种程度的生物已经没有继续生存的希望了。也许“牧羊人”制造的“镰刀”根本就无懈可击。我愤怒地将它向地上掷去,意料之中,它毫发无伤。
我没法再在实验室里待下去,走到了生物信息所外面的林荫道上。
宋慈还没有转去人类基因组研究院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傍晚时分走过这条林荫道,讨论实验的进展和各种细琐小事,然后夜色临近在路尽头分头走向左边和右边,走向各自的实验室。从春季梧桐长出新叶,到秋季暗红色的落叶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碎裂响声,我们一直这样走过。
我的脑海中回响着马尔特说“杂草”的声音。
“强弱在进化中总是变化的,你永远也不能断定一个物种的命运。一夜之间昆虫就崛起了,又有一天脊椎动物成为了陆地霸主,这也是我喜欢生物学的地方。”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在过去数不清的傍晚的某一个中,她说过,“人类的故事也是一样的,比如血色素沉积症,它和早衰症一样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病,现在被视作一种致命疾病,却很可能曾经在欧洲鼠疫横行的年代保护了欧洲人的祖先。你说,有没有可能哪一天我的早衰症也能风光一回呢?”
这固然是一个苦涩的玩笑,我心中却突然间升起了一丝希望——为什么“除草人”不用“镰刀”而选择了投毒,是来不及实施还是根本不能实施?早衰综合征的成因就是编码核纤层蛋白B的基因中,两个特定位置的碱基发生了突变,突变基因产生的毒性蛋白在细胞核内积累,引起DNA损伤。“镰刀”是否会将之视为受损的数据,对之网开一面。
我拦下了街上的的士,直奔妻子的实验室。
现在我的面前摆着基因突变的早衰小鼠,如果这一次仍然能被读取,那我将继续面对毫无希望的无差别尝试。
我触动了“镰刀”的底部,呆坐在椅子上,甚至不敢进行细胞切片。
一个小时过去了,小鼠仍然在笼子里活动。
三个小时过去了,早已超过了失去DNA的小鼠的生存极限。
我知道我成功了,“镰刀”没有收集早衰小鼠的基因,甚至很有可能,这两个特定位置的特定碱基就是终止读取的代码。我们能通过基因编辑获得生存的希望。
举行线上会议的时候,肖焰就坐在我身边。
一周前,她对我说,美国航天局截获了一条加密的宇宙信息,发信位置就在三光年以外。“‘牧羊人’很有可能就在地球家门口,各国政府坐不住了,要召开联合会议商讨对策。”三个月来我们拉近了不少距离,她说话不再像之前那样官方。
会上,有战略专家提议动用全球的核弹,形成一个核弹网络,一旦发射辐射范围将覆盖整个地表,以破坏所有地表基因作为威胁,迫使“牧羊人”放弃地球的遗传资源。
信息技术专家的提案是进行人脑上传,将整个人类社会从生物机体中转移到云端,在电子世界中实现人类的存续。但是在这一提案面前存在着过多的技术难关要攻克,受到了非难。
轮到我发言:“我的提案不是最优的提案,因为它没有办法保护绝大部分人类。我将我的提案视为最后的保底之法,它只能保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根据我的研究,‘牧羊人’的基因物质收集装置会将发生‘早衰突变’的基因视为一种冗余或是错误数据不予收集,给了我们偷生的可能。通过将正常基因编辑为‘早衰’基因,我们可以将一小部分人的基因物质保留下来,使他们继续生存,为人类留下火种。这是一个适用于小基数的方案,因为我们编辑基因所使用的技术在现阶段没有办法对成人进行改造,而只适用于对新生儿的胚胎,并且在未来的四年内也大概率难以实现突破。在我的方案中,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位能够得救。”
长久没有人说话,所有的画面都像断线了一样凝滞和沉寂。但在之后的表决中,我的提案却很快通过了。
我的方案被命名为“基因标记”。在最后的四年时间中,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在全球各地建起了“诺亚中心”,在其中对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获得的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而全世界的八位十六岁以上的早衰症患者接受了全部所需的技术训练和儿童养育培训,将要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承担那些“基因标记”后的儿童的抚育任务。对八千多种生物,包括微生物、植物、动物进行的“基因标记”也取得了成功,储存在各地“诺亚中心”的物种资源库里,静静等待着“牧羊人”和“羊”的到来,准备在“收割季”或称为“大洪水”之后作为生命的种子,延续地球的生机,支撑着人类继续生存下去。所有“基因标记”使用的技术仍然是宋慈团队当初开发出的技术。另外,基因制造和克隆技术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不久之后,也许不用一百年的时间,“诺亚”的新人们就能重现这个世界当下的样貌。
“你看到了吗?‘羊’!”肖焰打电话过来,声音激动,四年的合作让我们成为了朋友。
我坐在家中的阳台上,面前经过“基因标记”的那簇月季开得正好。五年之约,“牧羊人”如期而至。三分钟前,那台被称为“羊”的巨型电脑和宇宙舰船,遮蔽了月季之后的蓝色天空,就像一片无垢的、纯白云彩,不同的是,它以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标准几何形、覆盖了北半球的天空。从它降临在北半球到移向南半球,然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只用了30秒不到的时间。但它给地面的生物带来的不是丰沛生命的雨水,而是无情的死亡掠夺。在一瞬间,我感受到背部肌肉的一阵轻微抽搐,我知道我所有的DNA已经被夺走了。一把巨大的死神“镰刀”在过去的一秒内在我头上挥过,也在所有地球天空下的生物头顶投下了浓烈的阴影。楼下的绿树、花草和行人好像变成了一瞬的画片,喧闹的蝉鸣间仿佛出现了一个裂隙,然后一切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恢复如常。
失去DNA并不会让人的身体立马停止活动,最初,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还能继续工作,人还能行走、运动、说话,好像致命的丧失没有发生一样——直到那些死去的细胞和酶得不到补充,引发器官衰竭。
剩下的几个小时是人类最后的几个小时。
电话对面的肖焰听起来非常激动:“所有向它发射的激光武器和核弹连它最外围的屏障都没突破,真是绝了!”
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这个正经的女性平时的语气。我附和着。
“但是诺亚中心里的孩子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他们的基因还完整地留在他们身体里。你的方案成功了,枝鹰!”
我笑了,说,那真是太好了。
电话对面传来一阵杂音,和另外一个隐隐约约的女声,“好了,孩子们,别拉着肖主任了……我们来讲故事好不好?今天我们来讲‘牧羊人’的故事吧。”然后是一阵稚嫩的童音:“诶——”“可是听过好多次了——”
肖焰走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说:“孩子们太热情……”
我问:“刚刚说话的那个女性是早衰症患者?”
“没错。”肖焰的声音低沉了许多。对面沉默了半晌,说,“我还不想死,我还有大半个人生没有活够……”
我能够听出她的悲痛充满了克制。
过了一会儿,对面的声音又恢复如常:“我只是瞎说,你立马把刚刚听到的忘掉。”她在最后也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她就是这样的人。
“这场仗是我们没输,到最后起作用的不是基因,是人类的选择。”她咬牙切齿地说。
我赞同着。
“你不来‘诺亚中心’吗?我们几个组员决定一起迎接最后的时刻。”她问道。
我回答说,我想在自己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
挂断了电话,我看着眼前的月季,思绪游移,又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大一的课堂,老教授站在讲台上,说:“基因的演化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万亿条不同的道路不断分叉和交织,在40亿年的过往中是这样,也将如此延伸向无限的未来。”风扇的吱呀声贯穿了整个下午,我只觉得无聊,偶然间瞥到了斜前方的那个女生,室友凑过来说,那个新生孤僻又古怪。
在基因和生命的无限偶然之中,所有的复杂意识和心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牧羊人”追求着生命的超越,在旷渺无垠的宇宙中,想要抓住那遥不可及的真理的一线光芒。肖焰和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们,有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牺牲了生命中最后的时间,追求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
我在这无限的偶然之中追求着什么呢?
我恍惚间看到了大学里礼堂前那片盛开的月季。本科的岁月平静又琐碎,大二的课业不是很忙时,她会坐在月季前的长椅上读书。那时,没有人能够料想到后面发生的一切。
那一天,晚夕的暮光照射在交叠的花瓣上。我走到她面前,压抑着内心的忐忑,对她说,宋慈,我喜欢你,你能和我交往吗?
她惊讶地合起了手上的书本,抬起了面庞,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希冀,回答说,我是一个早衰症患者,我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消逝。和我在一起,没有未来,也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留下子嗣,连你的基因都没有办法流传下去。说到最后,她也语无伦次起来。
我抱住了她,说,我接受这一切,这是我做出的选择。
这是所有的偶然中唯一的必然,是在两端无边的黑暗中间短暂却又炫目的光明。
(本文获第三届星火杯全国高校科幻联合征文大赛优秀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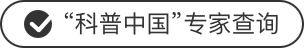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