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科幻研究新星论坛”于2021年4月18日圆满落幕,本次论坛共选拔出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等海内外的30位高校学子及青年学者进行主旨汇报发言。论坛同时受到了中国科技网、中华网、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作家网、中国科普作家网、中国资讯网、新华访谈网、科普中国、科创中国、深圳商报、大学生网报等权威媒体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重要反响。为进一步展现青年科幻研究新星的风采与面貌,凸显科幻研究的青春力量,论坛组委会对30位参会研究者进行了专访并集中推送,号召更多优秀青年学子加入其中。
2021
首届“科幻研究新星论坛“专访
VOL.1

吕广钊,伦敦大学学院(UCL)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伦敦中国科幻协会(Lond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Group, LCSFG)创始人及伦敦科幻研究协会(London Science FictionResearch Community, LSFRC)联合负责人,并且入选美国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SFRA)2021-2022年度“青年学者支持计划”(Support a New Scholar, SNS)。博士课题关注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科幻热”(The British SF Boom)以及“中国科幻新浪潮”(The Chinese New Wave),探讨两个科幻运动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背景。研究兴趣包括:中英当代科幻小说、乌托邦文学、末世文学等。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科幻的?您如何定义“科幻”?
吕广钊: 仔细回想的话,我第一次接触科幻应该是在二年级或者三年级。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有一天我在姥姥家玩,我妈从附近书店给我买了一本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青少版。我太喜欢了,没日没夜地看,反反复复地看,以至于我妈不得不把书藏起来,让我先写作业。不过后来,我却没有发展成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科幻迷,对于凡尔纳的兴趣并没有让我去找其它的科幻故事来读,反而更喜欢看科普类的作品。我知道有不少朋友阅科幻无数,不论谈起哪位作者,哪个时期,他们都如数家珍。说实话,我很难做到这一点,至今我仍然在补课,慢慢积累本该在小时候就读过的故事。至于“科幻”的定义,一百多年以来每位研究科幻的读者或许都有自己的想法,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性、概括性的定义。这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幻的“不可定义”。《弗兰肯斯坦》可以算作科幻(即便当时还没有“科幻”这个术语),《美丽新世界》可以算作科幻,《童年的终结》《黑暗的左手》《高堡奇人》《遗落的南境》以及我们自己的《三体》和《红色海洋》,这些作品的历史时代、叙事风格各自迥异,但它们都可以算是科幻小说。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让科幻小说作为一个文类,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活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拘泥于“科幻”的定义,不要纠结于什么是科幻,什么不是科幻,更不可因为某部科幻作品“在科学上不够严谨”而避之不及。在我看来,科幻与科学或者科普关系不大。科幻应当被视为我们对于现代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推演。自康德以降,关于“现代性”的哲学与文学探讨浩如烟海,祛魅后的人们诉诸理性与主体性,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巡视自己周遭的环境,于是理性和科学便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对科幻的期待。但当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消费”为核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将人们带入“后现代”的社会(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后现代性”是“现代性”在新的历史场域中的体现),而科幻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就拥有了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与叙事特征,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新浪潮与赛博朋克运动。与之类似的,现代性与生产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人们社会生产的重心正在从“消费”逐渐走向“产销”(Prosumption),即生产与消费的结合。这在我们当下的互联网经济中有着最为典型的表现。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参与生产,在休闲(刷微博)的同时也在创造资本价值(数据)。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也就看到科幻小说可能拥有的新的特征,人们对于后人类的探讨,也就代表了我们对于数字时代的审慎思考。所以,对于科幻的任何定义,都是基于历史的定义,都是不完整的定义。我们当然不能说,“啊那我们就不再定义科幻了”。我们当然要思考科幻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普遍特征与普遍诉求,但同时也要知道,这些特征和诉求是变化的,是辩证的,是历史化的。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在今天或许略显陈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的历史意义;同样,我们当今的社会背景,也在召唤着新的科幻形式与母题,这种在发展中显示出的潜力,不是某一种特定“定义”所能囊括的。
科幻在您的生活和学习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吕广钊: 作为一个把科幻研究作为博士课题的人,科幻在我的学习和生活里自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我和朋友Angela Chan在伦敦创建了“伦敦中国科幻协会”(Lond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Group,LCSFG),到今年四月恰好是两周年。这个想法的缘起是在2018年10月,那时陈楸帆和夏笳老师在伦敦南岸艺术中心(Southbank Centre)参加了一个讲座,我去旁听,而Angela就坐在我附近的位子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我们的协会在次年4月正式成立,每月举办一期主题研讨,旨在为身在伦敦,喜欢中文科幻作品的人们提供讨论和交流的平台。

左起依次为:英国科幻协会国际专员Dave Lally、陈楸帆、夏笳、著名译者Nicky Harman(照片为受访者拍摄)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也经过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在2020年3月,由于疫情,我们不得不将活动转至线上。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更多的受众,也能够邀请故事的原作者与我们一同讨论他们的小说。截至今日,我们共邀请到十三位科幻与奇幻作者,吸引了非常多读者与学者的关注。我们的推特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所以,科幻在我的生活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热情。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与英国科幻的交流做一点微小的贡献。
在什么机缘下开始研究科幻?与最初接触科幻相比,现在您对科幻的认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吕广钊: 初次参与科幻研究,还是在本科的时候。在2015年年底,我和朋友一起申报了一个大学生创新项目,我们做的课题是关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公意(卢梭)与群众暴力。那篇文章虽然在2016年就写完了,但直到去年才被当时的项目导师收录在一个论文集中。不过,那毕竟是本科写的,现在看来,不论观点还是文笔,都太过稚嫩(当然,现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除了这个,我本科的毕业论文(2016)写的是《三体》的翻译研究,从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着手。写得咋样咱们另说,不过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对我影响着实很大。时至今日,我对文学的整体认识还是基于当时对于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姚斯(Hans Robert Jauss)、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学者的理解。他们关于读者接受、视域融合、游移视点等概念的探讨,是我接触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步。真正萌生出“就把科幻作为博士课题吧!”这一可怕的想法,是我在伦敦写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那时为了赶时髦(以及偷懒),我沿用了一些在本科时萌生的想法,把“刘慈欣与克拉克的比较研究”作为了硕士的选题。在查文献的时候我发现,2017年的时候,关于中国(大陆)科幻的英文文献屈指可数,值得关注的重要论文只有1989年吴定柏老师为其《中国科幻小说选》(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撰写的绪论、2013年《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的中国科幻专刊,再就是宋明炜和李桦老师关于“中国科幻新浪潮”的探讨。那时我就想,中国科幻有如此多的内容亟待研究,不如我来为这一领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不仅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读博士的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关于中国科幻的讨论,越来越多优秀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方面让我非常欣喜,感受到了科幻研究这一领域的蓬勃生机,但另一方面,这也给了我不小的压力,我不禁会想,我自己的研究有何价值?有何独特之处?这使我回想起了本科论文中引用到的诠释学概念,我决定站在历史与社会生产关系这一角度,将科幻小说作为窗口,来探讨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与英国整体社会话语的变化。随着我对科幻文本的认识不断深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对科幻小说的探讨决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也不能囿于“科幻”这一文体本身。我们对于“中国科幻”的研究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关于“中国”的知识呢?我们对于“英国科幻”的研究能带来哪些关于“英国”的知识呢?同样,我们对于“黄金时代”、“新浪潮”、“赛博朋克”等题目的探讨,能为我们提供哪些关于这些运动背后的历史语境的思考呢?
参加首届“科幻研究新星论坛”有何感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吕广钊: 很遗憾由于时差,我没能够和大家一起参与“共时”的讨论,只能参加下午场。这要是放在以往,也就是熬一个通宵的事情,小意思。但现在年纪大了,不太行了,日益稀少的头发时刻提醒我一定要注意保命,切不可图一时之快。好在主办方分享了论坛录像,我趁这两天有时间,赶紧补了补课。正像几位评审老师提到的那样,我非常欣喜地发现,原来科幻研究早已不再是圈地自萌,而是真真切切的有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共同体,甚至还有了师门传承。而很多参会学者分享的论文,都很有前瞻性,也很有意义,我从中也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论坛”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台,让大家相互认识并熟悉。有交流,就会有火花;有火花,才能有创造。
您觉得本次论坛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们下一届论坛将会在线下举办,您能同时给一些建议吗?
吕广钊: 我希望能够添加答疑环节。这次论坛各位老师们的点评都非常有建设性,各有见地,不过在老师点评之外,我也希望能够与参会的诸位青年学者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我理解主办方这样安排的原因,时间有限,而且我们也建了微信群,可以随时联系。不过,在Q&A环节,我同样也对其他人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因此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在旁听他人提问的时候,我也可以学习如何从其它角度介入问题。这是我个人十分期待的。若论坛能在线下举办,那是再好不过了。线上的会议并不能够取代线下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据我过去的经验,最出色的灵感并不是来自别人正襟危坐时的有意分享,而是撸串吹水时的“胡言乱语”。所以,线下活动的意义是无法替代的。不过,这同样也意味着地理上的限制,舟车劳顿带来的困扰可能确实会让一些朋友望而却步。或许我们可以在线上与线下二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在设立线下会场的同时,也开放线上分享的可能性?
我们之前招募了一些热爱科幻研究的同学,让他们自选研究课题,以“协同创新合作”和“师带徒”的小组模式进行线上培养,您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行吗?您会不会愿意参与?
吕广钊: 我听说过这个项目!当时我还准备报名来着,不过,我后来忘记了……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在英国也有类似的活动,这边叫做“大师班”(master class),组织方会邀请几位学界大佬,带领年轻学者一起讨论课题(一般是收费的,还挺贵)。英国著名科幻研究期刊Foundation此前每年都会组织类似的活动(链接:https://www.sf-foundation.org/sff-marsterclass),但去年的活动因疫情取消,今年的活动形式他们还没商量好。至于咱们的活动,下次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参与!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学术爱好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您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可以分享一下。您关注同代人的科幻学术研究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吕广钊: 这两个问题我合在一起回答了,不过有几个词我不太明白,所以我找工作人员确认了一下。他们说,“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指的是“多人做研究不去深挖,套路格式都差不多,而且不结合现实,泛泛而谈”,而“经验的同质化”指的是“现在多数年轻的研究者和创作者接受的教育、经历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差别,可能不像过去那些研究者和创作者都有丰富而特别的人生阅历”。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两点。恰恰相反,我接触到的所有搞科幻研究的朋友,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学术热情和严谨性(也可能是尚未遭受社会毒打)。我有位朋友就在我隔壁学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研究的是中国当代科幻中的生态叙事。每次和她聊天,我都能学到非常多的新知识,深深为她中国文学方面的学术基础所折服。我们经常有一起开会的机会,每次她也都能针对我的课题提出尖锐、犀利、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与朋友的交流来看,我感受到的不是“不去深挖”,而是刨根问底;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针砭时弊,他们也没有脱离现实,而是在对科幻的研究中,表达了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关切。我也完全没有感受到“经验的同质化”。就像我们在论坛中看到的,三十位与会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和生活背景,即便探讨类似的课题甚至同一部作品,也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出真知灼见。我不敢说我观察到哪些“群体性特征”,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认识的青年学者们很多都有有趣的灵魂,也对新的事物抱有更加开放的心态。科幻研究的学者很少将文本局限在文本自身,而是更多的向外延展,将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空间之中。
感谢您对中国科幻发展研究及传播做出的贡献,希望继续为之努力,最后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吕广钊: 再次感谢主办方的辛苦工作!最后给大家分享《海底两万里》中的一句话吧(毕竟小时候看了那么多遍,还是能记住几句话的):“你只有探索才知道答案。”我很愿意在科幻研究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下去,也希望能够和这样一个优秀和充满活力的共同体保持交流!
采访 吴雨婷
整理 许艺琳 校对 赵文杰 排版 许艺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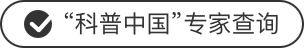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