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时,老师告诉我们说,治史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科学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的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
——王小波《未来世界》
《未来世界》
原书作者 | 王小波
本作收录于作品集《白银时代》中
Part.1
4月11日是王小波的忌日。如今距王小波逝世已有二十二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仍旧没有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他并不属于任何流派,但他的创作和死亡无疑是整个九十年代中举足轻重的文化事件。
或许属于王小波的永远是这样一个角落——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这些称号来自于李银河对王小波的那篇著名悼文,同时也框定了人们对王小波的想象:哪怕一个从未读过王小波的人,也必然听说过“特立独行的猪”或者“沉默的大多数”。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能经受住时间的淘洗,这已是至高无上的殊荣。
王小波的一系列头衔中并无“科幻作家”,但他确实写过一系列带有敌托邦色彩的幻想小说:其中,中篇小说《未来世界》于1995年发表于《花城》杂志,此时距离王小波生命的终结还有两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红拂夜奔》与《黄金时代》——大概是王小波最重要的两部作品;而此时的王小波则沉浸在理性思考的乐趣之中,创作上则逐渐走向僵化和停顿。
从内容上来看,《未来世界》有大量对《黄金时代》的重复:压抑乃至荒诞的时代背景;大量铺陈,甚至对情节发展举足轻重的性爱描写;对政治“黑话”敏感而戏谑的效仿。这种自我重复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出王小波创作晚期灵感的枯竭,但如果从科幻小说的角度切入,或许又将别有洞天。
Part.2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再就科幻的概念啰嗦几句。尽管对科幻小说的定义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有一点是无可动摇的:迄今为止,科幻小说仍旧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颠覆性)的文类。而最明显体现这一特点的,便是乌托邦与敌托邦小说。
参考科幻批评家达科·苏恩文的定义,我姑且将文学中的乌托邦定义为“对或然历史的一厢情愿的良性建构”。这个定义的反面中延伸出的便是敌托邦小说。
20世纪以来,乌托邦小说逐渐出现了被敌托邦取代的趋势,“敌托邦”这个词意味着走向反面失序的乌托邦——同样按照苏恩文的定义来说,乌托邦“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因而在小说中总是处于成长和完善期;而敌托邦则不同。它最大的特点便在于,永远都在一开始勾勒出一幅看似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蓝图。
对于乌托邦来说,主人公往往是美好世界的旁观者或认同者,而反面角色则对整个社会造成威胁;而在敌托邦中,由于社会已经尽善尽美,主人公所做出的任何触及其权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越轨——因此主人公要么是高举反抗大旗的英雄,要么是被动的,“没有选择的英雄”。
把《未来世界》归为敌托邦小说,并不是因为它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未来。如果按照对科幻的一般性认知来看,科幻中对应用科学,也就是技术,需要进行广泛的认知与构想——那么在《未来世界》之中,我们必然无法忽视其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存在。
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唯一具有未来感的便是“公司”,讽刺的是,这个世界中并没有任何科技上的进步,有的只是高效精准的管理体系。但如果我们将管理学也看做应用科学的一种(包括对社会科学以及横向科学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如应用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决策方法论、价值分析方法等),那么“公司”的设计便是这篇小说中最大的价值。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讨论。
Part.3
回到这篇小说。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有执照的,“根红苗正”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等等都完全地接受“公司”的管理。他们并非创造者,而是被动的按需生产者。如果你读过《黄金时代》,完全可以把此人看作其中的“王二”。
小说分为两个部分,上篇借“我”正在写作的传记,描写传记的主人公“我舅舅”其人;下篇则转向“我”本人——因为传记写作的过程中“我”犯了“直露错误”,整个人生被打入谷底,并开始接受“公司”的一系列改造——“重新安置”。在“重新安置”过程中,“我”的生活与数个同病相怜的女性发生交集,直至在一场耻辱的鞭刑(重新安置的最后阶段)后,回到原来的生活中,“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为止。
让这个故事从诸多不断相互重复的敌托邦小说中脱颖而出的,是王小波的智识与幽默。在文本中散落着“我”凭借历史学家这个身份对这个时代种种怪象的描述与讽刺:
我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这么说还是不明白。无数的史学同仁就是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是谁。
在这种描述中可以看出,王小波并不向这个敌托邦世界发起进攻。他刻意保持着与“我们”的距离,但也仅此而已。他所做的努力是让小说的主人公安然地按照这个世界的逻辑生存。
很难说这究竟该算是一种安之若素的处世之道,还是一种犬儒式的随波逐流,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在小说的下篇中,我们看到“我”终究还是因为“直露错误”而未能逃过一劫。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传记写作中的性爱描写过多,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源自监督体系之中的种种自我矛盾:
……现在我们有了一部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单无矛盾解释。”……但是历史法接着又规定说:“史料就是:1.文献;2.考古学的发现;3.历史学家的陈述。”……现在还有了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
它难免让人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种自相矛盾,互相嵌套的规章仿佛一个递归的程序,一旦踏入其中,必然陷入无限的自我循环。它存在的意义显然与历史本身无关。这样一个无法突围的迷宫本身便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你看不见边界,也看不到出路,因为它们是流动着,无迹可寻的。所有的雄心与叛逆都在突围的过程中被消磨殆尽了,如同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
Part.4
上篇中的“我舅舅”是个颇为有趣的人,在他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他是个数学天才,但自己的生活可谓一塌糊涂;他有着健美先生一般强壮的体魄,但却偏偏有颗衰朽的心脏。小说中提及舅舅的数学成就之处寥寥,但总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他的肌肉:
我舅舅赤着上身站在门口。我已经说过,我舅舅是虎体彪形的一条大汉,赤着上身很好看。
她只顾看我舅舅宽阔的胸膛,深凹的腹部,还有内裤上方凸显的六块腹肌。那条内裤窄窄的,里面兜了满满的一堆。
肌肉这个意象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同样是历史的:中国引入健美运动是在上个世纪初,其理念在于通过锻炼体魄来破除“东亚病夫”的招牌。当时的进步杂志甚至公益广告(如戒毒、戒嫖等)之中,随处可见赤裸上身,肌肉强健的男子,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面黄肌瘦,不成人形的“大烟鬼”。这其中寄寓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愿景;而在《未来世界》中,舅舅尽管有饱满的胸大肌和伟岸的阳具,其身体却衰弱不堪且有严重的心脏病,“全身上下似乎都流着暗红的静脉血”。
硕大的阳具难免让人悲观地想到,这种精神的缺陷将如同有致命缺陷的基因一般代代相传。健美的身躯就像花哨的铠甲,包裹着舅舅怯懦卑贱的内心。心脏病的隐喻难免让人想起,王小波本人也是因此而死。
王小波本人身材不算壮硕,形貌更实在算不得赏心悦目,但他是九十年代至今公认的“文化巨人”;舅舅更像是王小波本人的反面,健美的身材无法为他带来解放与拯救,反而使他被阉割过的精神显得更加可悲。
“我”呢?我身体苍白消瘦,是根所谓的“豆芽菜”,曾试图锻炼身体又吃不了苦。但“我”稍微懂得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之道,所以“我”在“公司”里终究混得还算不错,有房有钱,还给自己买了台小赛车。
尽管撰写舅舅的传记使我的生活一落千丈,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悲壮的反抗,更像是出于隐藏的叛逆之心所做出的一点儿危险的试探。这次越轨的写作直接将“我”的生活打入谷底,所有的财产都被“公司”没收,本人也被迫接受“重新安置”,为“公司”做着捉刀手等一系列屈辱的工作。在接受过鞭打屁股的终极羞辱,重新回到社会之后,“我”的精神阉割手术也正式宣告完成,如结尾所写的那样:
我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写《我的舅舅》那样的书,甚至更直露的书……但我完全懒得写任何书了。我还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爱她。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可能已经“比”(被动地成为同性恋)掉了。
文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意象便是小说中层出不穷的女性角色群。尽管在“我”和舅舅的生活中,她们走马观花般来了又去,但王小波同样也无意歌颂爱情。
在《第二次握手》等反映文革时期生活的经典小说(在彼时以地下文学的形态出现)中,爱情往往是救赎苦难,唤醒人性的灵药;但《未来世界》中,性爱变成了虚与委蛇的麻醉剂,不过是用以在无可作为的人生中打发时间。在消解了政治权威的同时,爱情或者人性的尊严也随之荡然无存。这难免让人想起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在那个全民族共有的红色梦魇中,权欲和性欲二者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沦为同等的狂欢。
Part.5
在《未来世界》之中,充满了经典敌托邦和黑色幽默小说的影子:隐藏的摄像头,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全盘瓦解,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法律与规则。在《1984》中,操纵这一切的是“老大哥”,一个无孔不入的集权政府;而在《未来世界》中,老大哥变成了为隐藏在幕后的集权政府打下手的“公司”。
让《未来世界》令人信服,在今日仍发挥启示意义的,是王小波敏锐的观察和辛辣的笔触。王小波的写作经验直接源自于文革,因此当这种经验转化入科幻写作的逻辑之时,这种转化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公司”是老大哥在中国的孪生兄弟,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更多中国特色,“公司”这一词汇也微妙地折射出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知识分子独到的悲观与疑虑。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管理并不像是《1984》中那样铁板一块。
《1984》中当然也描写在特权金字塔之中,塔尖的成员可以享有更多利益——比如喝真正的、上好的咖啡;而“公司”——实在让我无法不联想到国企——则总是留下无数的空子等着人钻,让人情世故有喘息的空间。“我”得到哲学资格证时的经历便印证了这一点。在哲学博士答辩中的过程极为有趣,摘抄在这里:
众所周知,我是免了资格考试去拿哲学博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招人恨。学位委员会的人势必在答辩时给我点颜色看看,故而做什么论文十分关键。假如我做科学哲学的论文,人家会从天体物理一直盘问到高深数学,稍有答不上,马上就会招来这样的评语:什么样的阿猫阿狗也来考博士!学两声狗叫,老子放你过去。我作的是历史哲学论文,结果他们搬出大篆,西夏文,玛雅文来叫我识,等到我识不出来时,他们便叫我自杀。我赖着不肯死,他们才说:知道你有后门我们惹不起。滚吧,让你通过了。
所谓的“后门”指的是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学妹。当时“我”的历史执照已经被连续记过,不得不为自己另谋后路,因此想到找这位关系暧昧的学妹来“走动走动”:
等到午餐时间,我和她去吃饭,顺便把给她买的绿宝石项链塞到她包里。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小子,不犯事你是记不得我呀。我当然记得她,她是个真正的虐待狂,动起手来没轻没重。如果求别人有用的话,决不能求她;但我的执照上已经有了三个洞,不求不行了。我说:我想考张哲学执照。她说:有事晚上到家里去谈吧。钥匙在老地方……带上一瓶人头马。
最后这场闹剧以“我”扮演“臭老九”,师妹扮演“红卫兵”的SM游戏告终,“我”也成功得到了执照。正是生动形象的受贿/走后门/托关系,让这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更为可信:虽然在此联系到人情社会等问题显得有些跑题,但还是容我指出:这种可信的细节好比烙铁。它在看似坚不可摧的制度肌体上刻下了自己的烙印,因而它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有效的。我们并不缺少对各种极端敌托邦社会的想象,但唯独缺少让这种想象与本土化的经验黏合的契机。
Part.6
上引描写中,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便是颇恶趣味的SM情节。这同样是一个王小波式的想象:在封闭的隐私空间(在此只能是想象中的隐私空间)之中,权威带来的的高压得以被暂时地消解;在SM过程中,残忍的批斗场景通过性虐待游戏,最终导向灵与肉的狂欢。
单独辟一小节提到这一点,是因为SM之中最重要的扮演属性,反映了王小波一直以来对乌托邦思考的结果。他认为乌托邦的罪行是一个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与破坏了别人的鲜活思想,这种破坏最直接有效的工具有两件:其一是无穷无尽的“黑话”(对话语的使用象征着阶级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其二则是如舞台剧般夸张的角色扮演。SM的过程则完美地对应了这两点:游戏中的“安全词”(在受虐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喊出安全词可以停止游戏)对应黑话,而施虐——受虐的对应则离不开暂时的假扮与沉浸。
这个简短的场景同样可被视为整篇小说的浓缩。整个《未来世界》中,“我舅舅”与整个社会,“我”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受虐与施虐的互动。由于缺乏必要的反抗,压迫可以沦为无伤大雅的游戏,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何尝不是“痛并快乐着”?
Part.7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科幻是启蒙的附庸,意在“追赶世界”,那么到了王小波写作《未来世界》的时代,似可宣告这种追赶的终结。尽管题目为“未来世界”,但这个世界里并没有未来,只有悲观的怀疑;它的视野也并非真的指向未来,而是在时刻警觉着过去的重演。而所谓的过去,无疑就是十年文革。
总的来说,王小波的写作是在处理文革历史与经验,但通过将文革经验以科幻的形式改头换面,他早已跳出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时代所开拓的写作方式。
邓晓芒曾指出,文革是一场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运动,只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每个整别人的人到头来都挨了整,所以它才不像过去那些运动一样总是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遭到了“全盘否定”。这个评价可谓犀利毒辣。
即使到了今天,仍旧有人在心心念念着文革的“光明面”(这一点绝非危言耸听),因此王小波的写作终究仍未失效,那些沉重的名头也还要再继续背下去。倘若王小波活到现在,我不知他该作何感想。
鲁迅万般希望自己在未来快些被人遗忘,但这一愿景至今未曾实现。不知何日王小波才会彻底过时,但我希望这一天快些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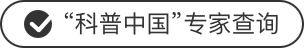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