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塔
--------------------------------------------------------------------------------
在身处的三维的空间里,岁月就像一把无情的刀,将皱纹刻在了我脸,将疾病注入了我磨损的身体机器。 一、
我的祖父是个立体画师,他的一生创造了无数栩栩如生的立体画作。比起这些画作,在我的眼里他的一生更是一个传奇。虽然外界对于我祖父的经历和作品都是正面评价,可古怪孤僻的性格和怪异举动在家庭里留下几乎都是一致的负面印象,不过我对他的绘画技艺倒是羡慕不已,也把他的画作当做是我绘画的楷模。
实际上,我的祖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学习绘画的导师。也正因为他的绘画教导,使得我的作品在各大高校的比赛里出类拔萃,但是一旦将我的创作摆在他的画作前,我仅有的那一点点骄傲瞬间就会荡然无存,我感觉我画出的都是一具具毫无生气的木偶,而他画出的却是活灵活现的世界。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一棵树,但却能从画作中感觉到风的气息。
二、
我还记得我那性情古怪的祖父在祖母辞世之前那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令我难以理解,也令我感到震惊,可好歹他是我的导师,我还能隐约‘谅解’他的这种做法,即便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谅解从何而来,又从何谈起。
他根本没有去医院看望病危的祖母意思,而只是整日将他自己反锁在画室内。我以为这是我的祖父在逃避即将面临的噩耗,可透过猫眼的窥孔偷看祖父的我却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祖父面带的微笑,整个人仿佛若无其事的站在画架前不停挥舞着他的画笔。
直到祖母老掉之时,他不仅没有接听我父亲的电话,也没有过来探望过辞世的祖母。更加离奇的是他竟然一声不吭的离家出走,仿佛像是个失踪人口那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所留下的也仅仅是一副新创作的图画,图画上是一片平静的出奇的海洋和岛屿的远影。然而除此之外,他没有向家人留下任何书信,就算是光脑上的电子档案。
“他怎么能这样自私!他是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家伙!”我的父亲浑身颤抖,只是捧着这幅画浑身发抖,虽然平常的他承认从前是祖父变卖绘画撑起了这个家,置办了这个家庭的各个产业,但是醉心艺术的他更是极少与他儿子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甚至父亲对祖父的了解也许不及我这个孙子。
“米洛维奇,也许伊凡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小声的在一旁劝解。我知道我父亲的颤抖是平静海洋上泛起的浪,预示着暴风雨随时将要来临。
“安德烈!你懂什么!他为嘴上说着爱你的祖母,可就连探望都做不到!都是这些画!这些画!我就当做他已经死了!我要葬了他,我要葬了这幅画!我当做祖母和他都已经死了!可怜的母亲竟在临死前还在念想着他们的初遇,他们的好!他在做什么!这就是他做的!”我的父亲米洛维奇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一滴泪水滴在了手捧的图画上,我看到了那立体的画上好像登时泛起了波浪,一抹夕阳在西落。
三、
祖父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和祖母的骨灰就葬在蒙特马里奥公墓。
只有每到祖父母的‘忌日’,我才会去十字架看看,为他俩送上鲜花。它们合葬的十字架上总会挂着陌生人的敬现的花圈,花圈上还挂着敬献者的名字纸片,我甚至还记得敬献的花圈名片落款为B·L的人是每年都会来祭拜。
我其实很想知道消失的祖父现在到底过的怎么样,可家人们对此的缄默和不愿提及好像是一扇已经关闭的大门挡住了我对此抱有的任何疑问,所以这种念头也只是在我作画的时候偶尔泛起。借着祖父教授给我的绘画知识和后天的锻炼,我成功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并凭借着一幅外界评价为栩栩如生的《3D彭罗斯阶梯》的立体绘画作品取得了立体绘画博士学位。
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3D彭罗斯阶梯》竟然最先得到的并不是学院导师的肯定,而是来自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关注和点赞。
不过顺利取得立体绘画博士学位的目的我是达到了,至于是学院导师还是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功劳,我就不甚关心了,对我而言这幅作品无非是巧妙利用光线明暗,将一个不可能存在的阶梯活灵活现的呈现在纸上,的确会让人产生某些方面的莫名其妙的错觉,也正因为这样打败了学院里那些如狼似虎的竞争对手。
立体绘画的这些方面我的确得感谢我的祖父对我绘画技艺的早期教育和指导,否则在这样的时代我能不能获得这撬开工作大门的一纸学位证明就是未知数了。在人工智能的被大范围运用的今天,原本就干着平常机械工作的学士们被社会淘汰已成事实,不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学士不进行深造,成为硕士或博士,那人就和人工智能根本没得比。
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会选用前者还是后者?相信这是一个根本毋需回答的问题。
四、
邮件Offer就在我取得学位的那个下午被发到了我的私人邮箱。这邮件Offer看上去更向一个颇为正式的国家邀请函,正是来自于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高额的薪水,个人画室,国家补助,半年假期,家人教育和医疗条款被罗列在邮件中。拿出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更有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专业人员接听了我的电话。
“我想问下...”我顿了顿,不知道从何说起,这种难以想象这种好运降临在我的头上令我感觉猝不及防,甚至让我感觉这是一场骗子精心针对我的骗局。让我情不自禁的联想起了脸书上经常收到的诈骗信件,“嗨,我是安提雅,是一名伊拉克石油富商的女儿,我的家庭正遭受当局迫害...”等诸如此类的信息。
“你想问我们是不是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是吧?安德烈·米洛维奇·弗拉基米尔。这里是空间研究中心总理办公室秘书贝朗特。”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更加吃惊,我甚至还没有自曝信息。
“你要知道,在国家面前,私人是没有秘密可言的。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任职邀请,我也难以想象一位刚取得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能被部长阁下专邀到我们中心任职。你的画作《3D彭罗斯阶梯》得到了我们中心科学家们的关注,想邀请你作为我们研究中心的专业立体画师。”对方回答的很详细,而且口音是纯粹的巴黎腔不含杂质。
“可据我所知,你们研究的是空间技术,卫星技术,运载火箭技术等。而招聘我一个只懂得绘制3D画作的博士有什么意义?”我仍旧对这个任职邀请抱着戒心,这根本和我的逻辑搭不成一条线。
“如果可以,有些事情你必须在任职以后与我们签署保密协议才可以知道。我相信我们会很快成为同事的,安德烈先生。我相信,为国家服务的好事你是不会拒绝的,如果你还有什么不相信,你可以看看窗外就知道有没有假了。”对方挂断了通讯,我猛然起身挑开了窗帘,插着空间研究中心小旗的黑色斯柯达反重力悬浮汽车已经悬停在窗外的半空中,那车辆的号牌正是来自国家空间研究中心,AA-010-AA。如假包换。
这样的任职,此类的邀请就像是在做梦。我做梦也没有想过一个立体绘画博士能够加入国人都羡慕的国家部门。
在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我见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那个与专门联系的贝朗特,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是人工智能的产物,一个高仿生机器人。他简单的给我办理了入职手续,又向我宣布一系列研究中心的规章制度,最后将一张纸质保密协议递到了我的手心,“在署名位置按下你的手指。然后,欢迎你加入研究中心大家庭。”
当我按下手印时,一只粗糙的手递到了我的面前,“欢迎你,年轻有为的安德烈先生,第一个真正在纸上画出彭罗斯阶梯的画家。我是空间学教授巴斯蒂安。你的祖父伊凡先生同样是个极其优秀的画家。”
我抬起头,向我伸出手的正是我在全息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国家首席教授,他现在就站在我的眼前,笑容温和含蓄,“看过您的书,也读过您的许多对于经典空间的论述。你好,巴斯蒂安老爹。”
五、
虽然绘画需要用到大量物理学知识,我对经典物理学知识的掌握也尚算丰富,但是在巴斯蒂安教授所掌握的高超物理学知识面前,就像小学生遇上了资深教授,我说的话他都懂,他说的话我却难以理解,甚至有时候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各种物理学公式和专有名词充斥在巴斯蒂安教授工作中,不像我只是按照巴斯蒂安指定的内容进行绘画创作。他会在闲暇时,轻轻的走入我的画室,立在身后沉默良久,或是和蔼的用物理学眼光来指出我构图中的硬伤。也正因为这点爱好,我们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也渐渐的在交流里彼此走近生活。
巴斯蒂安很少邀请别人与他共进晚餐,而我就是别人中的例外。
“安德烈,你知道我为什么很钟爱你的《3D彭罗斯阶梯》吗?”晚餐里,巴斯蒂安放下刀叉抬起了头。
“难道是因为他的构图。”
“这只是这幅画巧妙的一方面。虽然你的作品和你祖父伊凡先生相比水准还是差了很大一截。但是已经渐渐有了他画作的‘灵魂’。一种被称之为灵感的东西。”我知道,巴斯蒂安说的是实话,但对于这样的实话,我还是感觉有些尴尬,却并未否认。
“其实我要告诉你,你对你的这幅画作,命名是错误的,你应该叫他《4D彭罗斯阶梯》。”
“为什么这样说。我只是把这个充满悖论的阶梯以三维的方式以恰当的光影呈现在了欣赏者的面前。”我对巴斯蒂安的话相当疑惑,但这却让我想起了祖父离奇的消失,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
“你们立体绘画画师要在平面的纸张上让观看的人对绘制的物体产生立体的错觉。其本质就是利用光线的明暗和观察角度诱导这种错觉的出现。而彭罗斯阶梯在三维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维度却存在。”巴斯蒂安用尽量我能懂得的话说出了他的见解,还好不是公式。
“教授说的是我这幅画将观看者能产生四维空间的错觉?”我有些欣喜,我似乎隐隐约约明白了一件事。
“是的,这种错觉有利于让我找到灵感。一切物体之所以可见,其本质是因为有光。人类所生活的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与四维相交,也就是所谓空间裂缝存在特定的状态下,只是我们无法观察。就像你看到过世界上的诸多未解之谜,也许都和时空相关,一个人进入了另一个维度,所以他消失了。而你的这幅画就像是一把钥匙。”巴斯蒂安拖着下巴,仿佛陷入了沉思。
“难道...巴斯蒂安,我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的祖父事情,你的说法勾起了我曾经的回忆。对我祖父的回忆。”
“噢?”巴斯蒂安目光里射出的欣喜的光,“你的祖父的确死去的有些蹊跷,我几乎查遍了每所医院的资料,并未发现你祖父患病。这么多年来我也十分纳闷,可蒙特马里奥公墓的十字架却实实在在记录着他的名字。我之前告诉过你,我对你祖父的作品一直相当关注,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毕加索。不论其他人怎么看。”
“我知道了,你就是每年都会去祭奠我祖父的那个人!B·L就是你巴斯蒂安·吕利!”关于祖父的生平一时间竟向潮水般奔涌在家人为我筑起的‘壁障’,直至我感觉自己的脸开始发烧,继而这种热度传至了耳后根,终于,这壁障被汹涌的潮水击溃,对于祖父的思念像是决堤的洪水,泛滥了,“我的家人并不理解我的祖父,伊凡他是个永不放弃艺术追寻的人,我的父母不懂,我的亲戚们不懂!”
“是的,年轻的安德烈,你之所以现在能在这里,就是因为你追求的是和你祖父同样的目标--非凡。正因为你拥有这种可贵的精神和情怀,我从百万学子里选中了你。人能从一方面超过人工智能,也就只有精神和情怀了。你知道对于时空的概念,最早提出的并不是物理学家。而是爱因斯坦的老师,闵科夫斯基,一个具有深厚人文情怀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告诉我吧,安德烈,你祖父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巴斯蒂安的目光炯炯有神。
“他是消失了。消失在他的画室中。”我黯然答道,“也许难以想象,但--事实上的确如此。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是吧?谁又会相信这样离奇的故事。”
“也许真是发生在你周围的未解之谜。”银眉紧蹙的巴斯蒂安突然深吸了一口气,好似想到了什么,“那他为你们留下了什么?
“没有,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没有留下电子遗嘱。”我的回答一出,巴斯蒂安就立即垂下了头,仿佛对我的回答相当失望。
“吃吧。安德烈。”巴斯蒂安重新拿起了刀叉,随即陷入了沉默。
“啊,等等。巴斯蒂安,我想起来了!记得我祖父留下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我猛地用餐刀敲动餐盘,就连自己都被这清脆的当啷声吓了一大跳。
“那是什么画!?”巴斯蒂安激动了起来,他一拍脑袋,“也许这就是你祖父消失的关键所在!”
“好像是一幅平静的海洋,还有岛的远影。那是一副我祖父最擅长的立体画。”
“我懂了!科学是建立在大胆假设之下,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现象大胆的设想,你的《3D彭罗斯阶梯》让我产生了进入四维的错觉,是一幅对时空的抽象概念,就像是一个坐标,也是一把认知和理解四维时空的钥匙,然而我们却没有找到通往四维时空的门,而那副画也许就是一扇门,你的祖父在告诉你找到那里去的路,也许他早就知道了你的未来,而你的祖父消失也肯定不是偶然!也难怪我每次看到你祖父的作品总会感觉那些画作上的物体是真实存在的。我需要那副画。”
“可我们已经将它埋在了土里,永远陪伴着祖母。”
“我请求你,将它启出,就算为了整个国家!”
“可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假设。”我有些犹豫,从坟茔里取出祖父的画作,也许是对我死去祖母的亵渎。
“也许我们人类所追求的非凡超越,就在那里。安德烈。”巴斯蒂安落下了两行老泪,这两行老泪仿佛不是因哀求而产生,而是对科学的爱。
六、
尘封的作品,永远埋在土里,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
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在信仰与‘信仰’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我终于背着父母干了这样的蠢事。
蒙特马里奥公墓内,平静的葬着无数逝者,只有祖父母的墓穴处一点也不平静。
牧师们围住祖父母的安息处咏诵着神圣篇章,开启的墓穴内,祖母的棺椁依旧安静的放在那里,旁边纸卷是祖父离开时留下的画作。我颤抖的抚摸着祖母的棺椁,心中默念了无数声‘求主宽恕,祖母安息’。这才伸出了手去,颤颤巍巍的拿起了那卷祖父的画作将之放到一旁的密封袋中,铲土重掩了祖母棺木。
在回到空间研究中心的一路上,我的心情是忐忑的,我有些痛恨自己鲁莽的决定,我甚至认为自己猪狗不如。
回到画室后,巴斯蒂安已经在画室内静静等候,见我回来,他尴尬的站起了身,走到了我的身边,轻轻安慰着我。
“嗯,没事了。教授。”这样的应答声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甚至连我自己都快听不见。
“开始吧,安德烈。”一只粗糙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我真想抱着巴斯蒂安大哭一场。
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深吸了一口气,便着手开始了接下来的工作,将画室温度和湿度调整到了最适,从密封袋里取出了画卷,然后将之缓缓展开。
越是铺开祖父留下的这幅画,我的心情也就愈发的低落,画面由于长期掩埋于土壤里,如今已经是严重受潮,画面变成了数块一塌糊涂的毛边墨团,这幅画上哪里还有什么海,只有乱糟糟的一片。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终于控制不住泪水,嚎啕起来,泪水又一次滴在了这幅画上,可是如今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安德烈,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令人遗憾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修复这幅画,让他的部分重现,也许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
“拿去吧,巴斯蒂安,让这画离我远一点。现在,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没有扭头看巴斯蒂安,只是将画从桌面拿起,向一旁支去。
七、
还没有谁能完全修复我祖父伊凡的画作。即便修复的画作具有绘画大师的水准,但是却和原本的感觉截然不同。形似却不神似。即便巴斯蒂安将修复的画作重修了一次又一次。
“看来,这条研究开启空间方法的线索断了。”巴斯蒂安将经过了数十次修复的画作放在了我的画架上。
“是啊。我想教授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求科研的灵感了。话说回来,我祖父为什么会在消失前画这个风景?”上次的事件过去了很久,我已经走出了悲伤的阴影。
“这是希腊爱琴海。一个怡人而美丽的海洋,你看那岛屿远影,其中最大那个远影是克里特岛。不难想象伊凡是在何种角度描绘的景物。”
“噢?也难怪祖父会创作这样一幅海景,这是我祖父母爱情的起点,他们在40年前的爱琴海上认识了彼此--”我恍然大悟,原来我隐约谅解祖父行为的原因竟是因为他所描绘的这个地方。那时的我早就从祖母的口述里知道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浪漫的相会。啊,只是我今年的研究看来是白做喽。”巴斯蒂安轻轻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啊,半年假期就要到了。教授也许该去散散心,明年说不定会在研究上有所突破。”眼前的这个老人既是我工作中的领导,也是我真挚的忘年交。
“啊,我可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欧洲核子中心今年晚些时候要邀请我去参加学术会议,讨论下一次启动大型对撞机前机器将面临的安全问题。麻烦的事情真是一个接一个。这个讨论还得需要论证,做完这些工作估计要明年年初了。我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空去参加各种舞会,还有靓丽的女孩子的陪伴,不过话说回来,你也年纪不小了,该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另一半。”
“把她当做模特儿来绘画吗?”我笑着说道,“教授真是人老心不老啊。”
“其实我要告诉你,我追寻的是永恒。只是现在还差十万八千英里。”
我的画室里登时爆发出了阵阵欢笑,在与教授握手后,互道了再见。
八、
我并没有参加同学的聚会。而是驾驶着悬浮飞车,经过法国马赛,驶过了米兰,掠过了威尼斯,又沿着阿尔巴尼亚的海岸线,进入了希腊境内。最后,我将悬浮飞车驶入了卡拉迈,将之寄放在卡拉迈的立体停车场,去到了游轮公司包下了卡拉迈号游轮,追寻着祖父当年行进的航线在爱琴海上航行着。
这片海域果然如同祖父描绘的那样,清澈透明的海洋上只有偶尔才泛起一丝微浪,纵使耳边隆隆响着游轮那转动的马达声,也轰不破这海洋的宁静。我把画架架在了船头甲板上,握稳了笔刷,眺望着海天相接的地方,迎着习习的微风,感受着这海天一色的风景。
“左舷15。”粗鲁的吼声来自卡拉迈号大副,自船载喇叭中传出。船体开始微摆。我稍稍感觉有些晕眩,按住了画架支架。
“首侧推停车。”伴着车钟班的水手的呼声,马达停止了轰鸣,“放出锚链!”
数个水手朝海洋里丢下了船锚,微震的船体停止了摆动。周围陷入一片寂静。我抬首望向了眼前的地平线,果不其然出现了克里特岛的原因,这里的景象更是和祖父最后的画作出奇的一致。
提笔速写,我的画像是画中的画,立体世界中的立体世界跃然于我的纸上,我感受着微风那若有若无的声音,我捕捉着眼底收纳的一切,将这种稍纵即逝的感觉传递到我的画笔。
可就在这时,我的周围却响起了嘈杂的人声,我将视线移开了我的画作,我根本不知道除了卡拉迈号全体船员和我之外,还载着如此多的乘客。
“噢,天呐,我明明包了这艘游轮!”我有些懊恼,将画笔插入了画架笔筒,我并不是对游轮私搭其他乘客感到恼火,而是乘客们的欢闹打断了我的灵感,虽然我的画作就快完成,但是总感觉缺少一个点睛之笔!
不远处也正好有一个青年的画家,正和一个年轻女子嬉笑攀谈,我绕开了甲板上的人群,慢慢的走了过去,令我惊奇的是他正作着同样的画。
“这...”我看清了青年画家和年轻女子的脸,竟惊讶的说不出话。
那竟是我年轻时期的祖父和祖母!
我浑身不自觉的颤抖起来,我现在才注意到这里哪里还是卡拉迈号邮轮,这是我祖父当年乘坐的黑珍珠号!整船的男男女女使用的通讯工具竟然是早已被弃用的腕带式智能通讯装置。
“啊,你看,那个青年画家正在看我的画作,那人也画得不错,就是没有抓住这风景的神韵。”那年轻伊凡指着呆立在原地的我,我如梦似幻。
“那你不和他说说。你们都是追寻梦的人哩。”祖母发出的是银铃般的笑,脸颊上更是露出了那对迷人酒窝。
“噢,也好。算是一场交流。”年轻的祖父像我招着手,示意我走向前去。
我感觉这时我就像是个木偶,双腿摆脱了空白大脑的控制,迈足前进,“安德烈,伊凡你好。”
“啊,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我注意到了你似乎在向我寻求一些帮助。关于你的画作。”祖父朝祖母挤了挤眼。
“说实话,你们不仅有共通的爱好,还更是相像。别告诉我,你还有一个画家兄弟。伊凡。”祖母则害羞一笑,纤纤玉手掩住了嘴,可还是咯咯的笑出声来。
“我的兄弟可比不上这位年轻的画师。”耸肩的伊凡随即指向了他的画,“年轻人,你的画作缺少了一笔点睛,就在远方那将落未落的夕阳上。我注意到你的画作,兄弟,对你的作画水准我表示由衷敬佩。”
“谢谢你,伊‘万’。”我感觉自己的舌头都是僵硬的。
“不客气,安德烈先生,伊凡向你问好。这算是正式的介绍。”年轻的祖父像我伸出了友善的手。
“伊凡,伊凡。我就是你的子孙后代啊!”我的心中发出一阵呐喊,可还是不由自主的握住了它。
周围变得模糊,刹那间消失不见。我的身边是已经完成的画作,画中平静的海洋像是泛起了些许微波,那抹天边的夕阳仿佛就快落下地平线。
尾声、
怀揣着做好的画作,我回到了法国空间研究中心。
从不喝酒的巴斯蒂安就在我回到中心的当日与我把酒言欢,直到醉的人事不省。
打开四维空间的门和钥匙被我创作了出来,又由巴斯蒂安找到了进入的方法,可实践的事情一切停留在纸面,还得申请大量的国家资金和技术工程师付诸设计和实施,在人类即将步入四维时代的漫长岁月里,巴斯蒂安最终没有挺到时空之门开启的那天。可他在辞世时却是面带微笑的。
“我相信自己会在时空的某一个节点与你重逢。再见了,安德烈。我一生无憾。”这是巴斯蒂安·吕利临终对我说的话。
我捏住了这老人垂下的手,心怀遗憾。
在身处的三维的空间里,岁月就像一把无情的刀,将皱纹刻在了我脸,将疾病注入了我磨损的身体机器。
直到那一天,老眼昏花的我一脚摔在了中心的走廊上被人工智能抬进了医院,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疼痛席卷了我全身上下,以至于我动也不想动,只想从氧气面罩里呼吸那洁净的空气。
“祖父,祖母,你们一定还在某个时空中活着。眼看我就能来找你们,可是如今却做不到了。”我干咳着,我感觉我的肺就像被什么撕裂一样,就连我沉重的躯壳都向是在被锋利的刀刃在慢慢的寸割。
一个身影飘然而至。他慢慢靠近了我的床边,伸出了被颜料渗满指甲盖的手,轻轻抚上了我的额头。我看清了,那是一双擒满泪水的眼。
“是伊凡吗?哦,我亲爱的祖父。”我努力呼吸着好似衰竭的空气,嘴里蹦出了这一生的情感,“别人把你看成--毕加索。而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是的,我寻找了他一生,结果他在我生命最后一刻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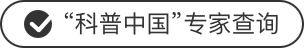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