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长路》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杨枫的《树上的九十亿个姐姐》。这篇作品的构思延续了杨枫一直以来灵动而奇诡的个人风格,但比起先前的《赛博酒馆的生命周期》与《金鱼大学》(文末可见链接)又更加“放飞自我”,多了些所谓的“阴间气质”。这种风格的渐变与作者对草野原原、圆城塔等作家的喜爱不无关系,也表现出杨枫一直以来对科幻写作之可能性的探索取得了成绩:作为一名活跃的新锐作家,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兄长凯旋而归时,小贝正蹲在河道边哭,一边哭,一边摇晃着姐姐。姐姐死了,肚皮凹陷地死去了。村子里已经很久没有收成了,谷仓见底后,兄长随人去外面搬救兵,再也没有回来。姐姐日复一日地带小贝外出觅食,挖河床,刨鼠洞,翻草根。河水蒸干这天,姐姐也蒸干了,她靠着河滩上的石冢,把最后几只蚂蚱递给小贝,说她累了,要歇一会,让小贝吃了东西再去转转。等小贝带着兄长失而复得的消息小跑回来时,她已经躺倒了,双眼落满灰尘,不再眨动。哭累了以后,小贝背起姐姐。他的肚子叫了起来,吃下的蝗虫来埋怨他抢占了姐姐的生机了。他回到家里,把姐姐轻轻放在父亲怀中,轻手轻脚,像在安置一片羽毛。原本喜庆的氛围顿时暗淡下去。母亲嚎啕大哭,父亲则无声落泪,兄长带来的神婆也念起了咒语,在村民的沉默中为逝者送终。 过了一会儿,归来不久的兄长走上前,搀起父母。 “人死不能复生。”他轻声说。“而且,这样一来,咱们就有活路了。”“来,把姐姐埋了吧。”神婆念完咒语,兄长示意小贝去取铁锹,等万事俱备,便开始指挥村民安葬死者。眼前的兄长和出发前不一样了,身材变壮实了,眼神变得像鹰,看谁都像猎物。小贝不喜欢这副模样。从兄长那里,他觉察不到感情。姐姐死了,兄长甚至都没有流泪,仿佛她只是个随处可见的陌生女人。就连她的死也仿佛在兄长的预料之中,尽管按照他的说法,这不过是个不幸却又幸运的巧合而已。遵照兄长的指示,村民把姐姐埋在了村子中央。神婆在此作了一夜的法,披头散发,将试管和培养皿中的溶液浇灌在坟头。巫术只对新鲜尸体有效,这是人们从神婆的疯言疯语中解读出的说法。夜半三更,起风了,仿佛要下雨,但是到了第二天,土地却依旧龟裂纵横。绝望的村民们再度聚集在姐姐下葬的广场上,要向兄长讨说法,争执间,发现坟头生出了一棵树,枝丫稚嫩,却执意要同上苍对抗,不到半个时辰,树冠下已能供人乘凉。兄长说,这就是他找回的法子。在漫长的求索中,他走遍每一座困顿至死的村镇和城市,最终倒在海床上等死。就在那时,疯疯癫癫的神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救活了他,接着,在昙花一现的清醒时段,告诉了他这个拯救家园的办法。又过了一天,大树开花了,花瓣有白有紫。小贝认得它们。干旱尚未来临时,姐姐会调皮地给他编小辫,然后在上面缀满雏菊和丁香。从神树的性状里,他看到了姐姐的影子。而神树也迅速回应了他的印象,一夜过后,褪去满树繁花,枝叶间生出累累硕果,每一枚果实都和婴儿时候的姐姐一模一样。 兄长摘下了一个姐姐,张嘴咬下一口,却被母亲劈手打落在地。 “你做什么!”她反手又是一巴掌。 “妈,放心——这是水果,只是长得像人。刚回来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可能会有点吓人吗?别担心,没事的。”兄长说完,又摘下一个来,塞给旁边的村民,自己则捡起地上的,掸落尘土,吮吸起腹腔里脏器形状的果肉。接过果实的村民左顾右盼,最后闭上眼,咬了一小口,接着是一大口,然后吃掉了整条手臂。看着他大快朵颐,其他人也终于按捺不住腹部的阵痛,争先恐后地狼吞虎咽起来。最后,小贝的父母也屈服了。他们摘下了果子,一边哭,一边吞咽。小贝也加入了他们。他接过兄长递来的娃娃果,咬了一口,唇齿间顿时清香四溢。死去的姐姐在他的嘴里复活了,像夏季的阳光,如砂糖般甜蜜。小贝又哭了。在河滩上觅食时,他曾经许诺过要守护姐姐,如今他却把誓言吃下了肚,只是为了活下去。 童年结束了。盛宴临近终止时,兄长让小贝收集四散的果核和种子。 “我要再出去一趟,去附近的几个村子,把这些带给他们。”他说着,摸了摸小贝的头,“我知道这种方式很难让你接受,毕竟那是你的姐姐。但世界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如果有别的办法,谁想这样呢?” 那也是你的姐姐。小贝本想这样说,却只是埋头攒了一捧骨殖,装进兄长撑开的口袋里。临走前,兄长还嘱咐村民都装些果核,回家种在地里。所有人都照做了,其中也包括小贝的父母。小贝本来还想再做些什么,来纪念这个被姐姐拯救的日子,但是饱食感引发的困倦却淹没了他,让他在回到家后不久,便在母亲的怀里沉沉睡去了。树上没有果子了,光秃秃的。骸骨形状的果核,和果皮外的毛发间镶嵌的种子,都被悉数埋进地里。手舞足蹈的神婆已经不知去向,在失踪前,曾经口吐白沫地嚷嚷着:第一个牺牲的人,将会为所有人带来救赎。如今这救赎已经来临,人们只要尽本分、遵天命便好。当晚,小贝趴在炕头,感受着母亲的体温,做了一个梦。梦里,姐姐变成了山一样的巨人,开天辟地,又倒在地上,躯壳幻化成世间万物。他躺在姐姐的胸口,看着树苗一粒粒钻出自己的身体,渐渐喘不上气。他在窒息中惊醒,天已大亮,屋外绿树如茵,每棵树上都结满了大大小小的姐姐,乌黑的秀发从土壤里喷涌而出,如黑色芒草般四处释放着奔腾的生命。他穿好衣服,下地去帮父母耕田。梦境却不依不饶,在他的裤裆里留下了一滩湿漉漉的成长印迹。 
小贝的村子地处盆地中央,交通闭塞。树林发育这段时间,兄长遍历附近村落,最终,再度翻越环绕盆地的群山,进入不为村民所知的世界。兄长直到入冬才回来。在此期间,小贝一直在精心呵护每一棵树。日夜吞下的果实凝结成沉甸甸的原罪。只有站在树下,看着树苗们茁壮成长,他才能获得片刻安心。在他的呵护下,树上的姐姐们渐渐长成了妙龄少女。大树和大树之间仿佛心有灵犀,让果实们维持着神秘的年龄同步。兄长回来时,小贝正在给姐姐们套过冬用的棉袄。棉袄是他用乌发草织的,比棉麻穿着更暖和。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他正在清点人数,忽然听见鞋子摩擦草叶的声音,便转过身来,刚好看到兄长带着十几名陌生青年赶向村中大屋。他上前问候兄长,兄长却叫他别说没用的,叫村里的人一起来。他腰间别着长刀短刃,额角多了两道伤疤,衣着变华丽了,眼神却变得更加阴郁。身后的青年们也大抵如此,身材壮硕,遍体鳞伤,比小贝更像兄长的孪生兄弟。在大屋里,兄长彻底变了。小贝印象里的兄长少言寡语,忠心耿耿,为了家人,只管埋头苦干。但是眼前的兄长却面朝满屋父老乡亲,侃侃而谈,不时喝口水,环顾四周,像是在确认谁是自己人,谁不是。兄长端坐在长桌一侧,开始讲故事,说他带出去的树种和草籽一出盆地便不管用了。这些植物只能种在村子附近,离村子越远,长势越差,等翻过山脉,就再也不出芽了。好在他在路上遇到了运输能力高强的商人联盟,后者愿意帮忙把姐姐树和乌发草的衍生产品运输到更远的地方。为了配合他们,村民们需要做的,只是建设工厂,规模化各家正在进行的耕种作业,从而让姐姐树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村民们咀嚼着兄长描绘的愿景。一些人品尝出了其中的血腥,向兄长投来敌视的目光。他们身上的乌黑长袍和胯下新鲜的实木座椅却出卖了他们,让他们在兄长的扫视中缓缓垂下头,不再多嘴。“世道已经变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大陆上很多人都会死。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们活了下来,我们有责任让更多人也活下来。这是我们赎罪的方式。”兄长把手掌压在刀柄上。他的语言收买了一些人,他的手收买了另一些人。他带来的年轻人守在门口,冷漠地注视着屋里发生的一切。“接下来我会交代我的计划,不过在这之前,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加盟。”兄长再度扫视四周。屋里起先一片沉默,过了一会,一只手举了起来,又一只手举了起来,然后是第三只,第四只,渐渐超过半数。“好。我不会为难剩下的人,你们可以走了。”一些没举手的人离开了,一些没举手的人留在了屋里。小贝本想上前问兄长他到底怎么了,却被兄长身边的随从推了回去。兄长对此并不加以阻拦,甚至对那人点头以示认可。小贝对此感到骇然,旋即感到心灰意冷。他随家人走出屋外,走了一会,猛然跪在地上,呕出半口未消化的果子,从此下定决心,不再过问兄长的任何行径。从这以后,兄长便在村子里住下了。他不再回家,而是在村外圈了一块地,在那里风餐露宿。在大半个村子的帮助下,他们迅速建好车间,和随后赶来的商队代表进行接洽,完成了第一批样品的展示和交付。交易现场,他们带来了一箱脱骨果脯,一桶鲜榨饮料,还有用果核、草叶和原木制成的桌椅板凳。商人们很满意,带走了全部货物。贸易路线走通了,工厂从此日夜轰鸣。人们从树上摘下一批又一批姐姐,扒光外衣,装箱送进工厂。村子渐渐被分割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果树林立,另一个区域血肉横飞。园丁们剪断果实头顶的脐带,将她们成批运往车间。车间里的工人则负责抽取体液,剥下果肉晾干,再挑选出符合规格的骨骼、皮肤,送到加工区域,最终将它们制成食物、砖瓦、日用品和奇形怪状的首饰。产品一部分被村民自行消化,更多的批次则被人打点整齐,交付给前来取货的商人,带到外面的世界去。兄长还在继续讲故事,这些故事比以往的那些更加隐晦,但个个掷地有声。诸如他在处决工贼与侵入者时的愤慨指控;诸如他在拥立新村长时的激昂陈词;诸如他在热情款待渐渐渗透进村落的武装商队时,在宴席间,在宅屋后发出的窃窃私语。这些故事风暴一般席卷整片盆地,把越来越多的人吹向兄长的阵营。低地果园的消息也随之蔓延开来。陆续有逃荒者翻山越岭来此定居,皈依在兄长的麾下。他的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包围了自由人的林场。一些新入伍的佣兵开始僭越兄长曾经划下的界限,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目睹这一切,小贝时常感到自己脚下已不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无底深渊。一股愤怒自深渊中徐徐升起。他觉得兄长背叛了姐姐,村民也背叛了姐姐,只有他才是姐姐真正的守护者。姐姐是他的,只有他配得上她。他渐渐陷入偏执,疑神疑鬼,开始日夜守在林间,逢人便撵,每晚都做着关于姐姐的梦。他打着只属于他的战争,与此同时,另一场战争正在暗中酝酿。小贝看不见这场战争的蛛丝马迹,看不见森林里游走的人影和根系间埋藏着的斧钺钩叉,看不见他家人向兄长俯首称臣的场面,也看不见他兄长仍旧阴沉凌厉的面容。他看见的只有姐姐,树上的姐姐,树下的姐姐。在夜不归宿的时光里,他建起一座林间棚屋,携带全部家当住了进去。姐姐的照片被他装裱在姐姐做成的相框里,相框被他放在姐姐做成的橱柜上面。餐桌上的碗筷是用姐姐烧制成的,盘子里的肉是姐姐的心肝和肠胃。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在这灰褐色和肉红色交织的空间里,姐姐辐射出的生命力令小贝如痴如醉。他偶尔会在林间睡着,耳边回荡着姐姐的呼唤,醒来以后,凉风习习,少女们在头顶轻轻摇动,仿佛一串串起舞的风铃。 
春天来了,夏季去了,兄长的计划随着秋日临近,渐渐成熟。靠着一年来的辛苦和忠诚,他请来了商人们的首领,还说服了他,将联盟的根据地从干涸的海角迁至林地。立秋当日,首领坐在轿子里,口中噙着风干的手指,身后旌旗猎猎。漫长的交接和转移工作已经结束。在前往新家的路上,他终于得以深沉品味口中少女的味道。万灵凋敝前,他曾吃下数不清的美食,上至皇家御膳,下至虫豸蛇蝎。对美味,他早已没了概念,就连服用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无法带给他的舌头任何快感。但是少女的体香却唤醒了他的味蕾,让他开始幻想:在旅途的终点,究竟有何等珍馐在等他享用。这幻想令首领老去了,变得和善了,在得到小贝兄长的热情接见时,也只是慵懒地靠在太师椅里,任由眼前这踏实稳重的年轻人安排一切,自己则靠在主宾席上,笑纳下属呈上的一份份贡物。 宴席行至中途,一只手扳住了首领的下颏。他伸手去抓它,口中涌出大股金属味道。一只手把匕首缓缓送进他的肚腩,另一只手则持刀割开他裸露的喉咙。首领的一生就这样随着尚未被他消化的食物飞散开去,一部分飞向天空,另一部分涂在地上。早已倒戈的侍从们履行了叛徒的义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迅速爆发,又迅速结束。末了,兄长摘下已故首领的戒指和项链,装点在自己的身上,站在焚烧尸体的篝火前,开始讲述他在第二次离开盆地以后,被商队俘虏,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他列数商队的罪状,始于他们在贫瘠末世上的掠夺行径,提到了自己为了不让盗匪般的联盟掠夺盆地而做出的牺牲,赞赏他身边这些和他同甘共苦的兄弟,并感谢长久以来一直配合他推动这场计划的所有人。而在最后,他宣布:由商人中饱私囊的旧秩序已经解体,他将组织联盟的残余力量,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拯救芸芸众生。他的演讲结束时,大地忽然剧烈颤抖起来,在翡翠海似的丛林深处,一棵树发了疯,枝杈开始向四面八方凶猛冲刺,转眼间便鲸吞了半片林场。树与草的根割破土地,钻进群山深处。它们的枝干合而为一,形成一棵前所未见的齐天建木。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但兄长仍旧对惶恐不安的听众说:此乃吉兆。他看到了人群中的父母,唤他们来他身边,问他们小贝在哪里。带着对这已然陌生的救世主的困惑和无力,父母二人遥指建木方向。于是兄长明白了:眼前景观乃是小贝的造物。他向人群高呼小贝的名字,说新世界的诞生也有自己弟弟的一份功劳,然后在欢呼声中回到据点。等到夜深时分,他带上灯笼、匕首和贴身侍卫,前往密林深处。建木的根系错综复杂,俨然一片墨绿色的迷宫。枝干排山倒海向他们挤压过来,乌黑细密的草叶纠缠起众人的脚掌,让他们在披荆斩棘中渐渐耗尽体力。尽管如此,兄长却依旧稳步前进,而他的侍卫们也无声无息地跟在身后,保护他们的主人。风渐渐弱了,树根盘曲成树洞,阻隔了空气的流通。一名侍卫注意到上方的果实形状有异,便举高灯笼,陡然看见一串白皙脚趾悬挂在头顶。他心头一震,灯笼掉在了地上,引得一行人纷纷驻足。他们这才注意到,少女们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凹凸有致的少妇,身材丰满,面容圆润。越过这些悬挂在树洞顶端的饱满人形,他们还看到了树皮上的朵朵花纹。花纹中雕刻着女孩和男孩嬉戏打闹的场面,一幅幅图景绵延向前,引领众人来到建木中央的巨大空洞。在这里,吃奶的女孩,采花的女孩,跳舞的女孩,耕作的女孩,飞翔的女孩,潜泳的女孩,出嫁的女孩,女孩生下的女孩,以及和她们做着或相同或不同事情的男孩们,肩并肩,手挽手,千千万万,纷纷扬扬飞向树洞上方,消失在洞顶的一方星空里。 兄长站在洞穴中央,环顾四周。一向擅长讲故事的他,反常地陷入了沉默。他没有向侍卫们解释他沉默的原因,侍卫们也任由他私藏他的秘密。他们在沉默中回到据点,让今晚的所见所闻成为各自心中的谜题。他们没能找到小贝。在先前的革命里,他们也没能救出神婆。天亮了,对夜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世人们渐次醒来。他们不知道革命背后的成功与失败,只是在这个与旧世界不尽相同的新世界里把兄长奉为主宰,一如既往地向主宰提出期待,也迎合主宰的期待,将姐姐树的血肉播撒到更远的地方。大陆虽然还是那个河涸海枯,一滴雨也不下的大陆,却久违地喧嚣起来。而在喧哗声传不到的地方,那终究没能找到的小贝,渐渐变成了一段民间传说。 
兄长也有自己的故事——在缄口不言处,故事自在萌生。 继承天命之后,他收获了自己的随从:宰相、将军、贴身护卫、书记员、祭司、教育长官、勤务部长、宣传处主任、库房守门人、厨师、丑角、士兵、仪仗队号手……人们在救世主身旁找寻到各自的位置,用一言一行拓展、耕耘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在浩渺无际的森林中,兄长的身世裂变了,从一千种男孩,变成一万种勇士,十万种救主,最终进化成坐拥百万形象的皇帝。童谣、传奇、颂歌、教典、诗词、笑话……硕果累累的世界因故事而变得丰满充盈。在万千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版本深得内阁人士的认可。这个故事说:在皇帝的眼中,世界一直在变,快得令人目眩。故事说,起初,还是男孩的皇帝尚未目睹大千世界,只想继承父母的衣钵,传宗接代,支撑家庭。他有一个年轻时当过兵的叔父,平日里总是絮絮叨叨地讲述着五花八门的英雄故事。他喜欢那些故事,它们在闲暇时光里让他开心,偶尔会让他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但也仅此而已。和河边嘎嘎大叫的鸭群相比,英雄就像天上的云,风一吹,便散了。故事说,男孩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直到灾荒掀翻了他的生活,把更大的责任安置在他的肩上。他随叔父离开村子,第一次想要成为英雄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在四次无功而返的求救以后,拯救世界的天真愿望变得现实了。他们洗劫了另一个村子,在混乱中,他杀死了一个给过他面包和水的女孩。后来,他们又在存粮再次耗尽时,抽签决定要杀谁吃掉。他那满腹传奇的叔父在抓阄中做了弊,骗他拿到了最短的签。于是,他在逃出生天之后,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是隐藏自己的真心,不再相信任何人;第二是效仿叔父,把故事当成最锋利的武器。故事说,从那时起,男孩变成了勇者。故事还说,男孩拯救世界的愿望并没消退,反而在他遇见神婆后,变得坚如磐石。那个被他杀死的女孩成了他身边的幽灵,时刻提醒着他:世界很大,他要拯救的远不只自己的家人和村子。姐姐树的诞生让他向梦想前进了一大步,可是他却又犯了一个不成熟的错误,寄希望于商人联盟。他向他们奉上以他妹妹为祭品换来的果物,但是商人们的目光却让他再次回想起屠杀同胞时,自己同伴眼底的神采。商人们用力量征服了他,他不得不花费了比预期更久的时间,付出了更加沉痛的代价,才终于收回了权力,蜕变为救世主。 在故事的末尾,世界依然在变。建木诞生后,树和草都觉醒了,挣脱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刺穿外围山脉,向外野蛮生长。皇帝本以为自己是一切的引导者,却渐渐发现曾经被他视作兵器的故事慢慢变成了盾牌,他打造的新秩序也沦为了树海的附着物。作者生动准确地描绘了皇帝登基之后的世界图景,从而让皇帝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而皇帝的沉默寡言,又似乎隐隐在对作者说:是的,你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皇帝依然是个坚定的行动派。在忠心耿耿的卫士和谋臣的帮助下,他开始建立属于他的丰功伟绩。他们引进了更加科学的管理手段,改革市场制度和土地所有制。在他们的推动下,姐姐树以坚韧不拔的生存能力,扎根在大陆的每一片土地上,甚至淹没了海床,扑向其他地质板块,直至覆盖整颗星球。数以百万计的流水线开始滚滚奔腾,数十亿姐姐滚过刀锋,支离破碎。从天上看,这颗星球终于不再是一片褐黄了,披上了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海洋。最终,几场或大或小的兼并战争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大一统国家诞生了。帝国的国旗是三色旗,沿用大地的红、绿、黑三原色。帝国的首都攀附在林木上。人们在树干上开洞,以为房屋。城市的主干缀满绿叶,四下里挂着的姐姐们在高楼风中摇摆不止,远远望去,仿佛一场空前绝后的绞首盛宴。“妈妈,树上的阿姨是谁呀?”有时,会有孩子这样问。问答,问答,在父母和子女的你问我答中,在男女老少的口口相传中,一场新的战争打响了,故事的混战。敌对故事的主角有时是林间鬼魂,有时是身为隐者和圣人的小贝,有时是奄奄一息的商人联盟,已故的神婆,甚至是早已长眠于树下,变成创世神明的初始祭品。他们不如皇帝丰满,也不如他真实,但他们的人物弧光却同样引人入胜。这些故事脱胎于小贝遗留在树洞中的飞天壁画,变成了皇帝治下的在野叙事。出人意料的是,皇帝对脱缰的故事们表现出惊人的包容,甚至将收容壁画的中央树洞开辟成圣地,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瞻仰。他因而获得了至善明君的新称号。他娶了旧日邻国的女王为妻,将种子播撒进她的体内;他的故事则与野生故事联姻,繁衍出了更多子孙后代。公主满月时,有位天才的吟游诗人甚至提出,皇帝是被放逐的父神,将在女儿长大成人那天死去,取代树上的母神,泽被四海八荒。在皇室听不到的地方,这位醉酒的歌者放声高唱。在他的头顶,鸟群呼啸而下,又被路过的骑手们惊扰,逃向四面八方。诗人不悦地暂停吟唱,目送马群离去,又唱起另一支关于公主的歌。他躺在丰乳肥臀堆起的小山上,赞颂生命的诞生与传承,尚不知远方,小小的生命已经夭折,而刚刚离去的骑士正在赶赴葬礼现场。皇家陵园一片狼藉,公主的墓大敞四开。骑士翻身下马,加入他的同行——远道而来的智者们。他们围在空空如也的坟坑边,讨论着神婆留下的只言片语,和公主下葬后不久,从地下传来的神秘声音。棺木不见了,尸体也不见了,土壤中只剩下一缕缕纤细草根,有些盘绕在树根上,有些刺进树根里,有些小手般指向天空。惊魂未定的皇后嚎啕大哭,皇帝站在一旁,仍旧沉默不语。而他的下属们,也陷入了沉默。于是,故事继续野蛮生长,打着永无休止的仗,被世界塑造,也塑造世界。故事说,果实的演化遵循着人类的生老病死,虽然正值壮年,却终将老去。届时,帝国将迎来真正的危机。故事说,皇帝终于走出了丧女之痛,正在筹备第二次拯救,以基因工程之秘术,让果树重返青春。所有的数字都在兆示经济的发展,平均寿命的增长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未来可期,未来光辉璀璨。故事说,埋到地里的一切都会迅速被草木吸干,还养分于天地。树和草的根系已经遍布地下世界。斩断一棵树的根,其他植株的地下部分也足以支持其残躯存活。养育世人的森林正在吸血鬼般摄取星球的养分。面对这些现象,智者们也无可奈何。神婆的智慧已经是失落的巫术,而这世上的科技体系早已在漫长的荒芜中烟消云散,他们无力继承她的衣钵。故事说,神婆没有死,而是被皇帝秘密保护了起来。如今,他放弃了无用的智者,正在全力医治神婆。在名医的悉心照料下,神婆已有好转的迹象。巡夜人甚至偶尔会看到她在塔楼上手舞足蹈,摆弄着五花八门的实验仪器,搔首弄姿,和旧世传说一模一样。故事说,世人与姐姐树已经密不可分,那些妄图铲平大树的派系不是抱着拒绝食人的理念活活饿死,就是发现和真正的食人生番相比,现下的生活更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欣然放弃对旧世道德的追求,甚至发展出与果实交媾的风俗传统。故事说,皇帝没有重振雄风,神婆也没有复活。故事说,过去的故事都是真的,姐姐树真的老了。于是,一些故事输了,另一些故事赢了。皇帝老了,他的树也老了。 皇帝几乎是和他的树一起老去的。 他稀疏的头发开始褪色那天,田野里的乌发草也褪色了。漫山遍野呈现出灰败的颜色,树上果实也早已是陈年老妪,尽管还能吃,口感却大打折扣。他的臣子在努力回应民众的困惑和忧愁,指出国库里已经预留了足够分量的食物,部长们也在努力研究应对危机的方法。但不论是朝堂内外,都郁结着浓郁的颓废气息。面对着这和自己一起老去的世界,皇帝不禁烦躁起来。他遣散了从智者中选拔的助手,脱下神婆脏兮兮的白大褂,离开塔楼,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在困倦中,皇帝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在一个贫瘠的午后打倒了一名瘦小的男孩,骑在男孩的背上。可是那男孩却沉进地里,又从远方升上了半空,长出翅膀飞走了。他正要去追那男孩,梦又切换了舞台,将镜头转向一个躺在树下的人影。在人影身旁,成群结队的年轻女孩欢声笑语,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纵情奔跑,踏在乌黑的草海上面,仿佛一群海豚,手舞足蹈,自由自在。梦境里吹过一阵寒风,吹乱了皇帝的脑电波。他轻哼一声,悠然转醒,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税务报表和商业合同,兀自出神。忽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砰,砰,砰,房门鼓声雷动。他问是谁,何事,怎么了。侍卫长在门外气喘吁吁,说建木出大事了,请皇帝赶快去看看。皇帝起身来到露台,眼前所见令他感到毛发倒竖。目之所及的天地间,一场龙卷风肆虐后的余兴表演正在上演。干瘪的果实噼里啪啦从树上坠下,摔成一滩滩血浆,一团团皮囊骨肉。有人坐在尸山上恸哭,有人张开大网,接住噗噗坠落的果子,他们的孩子们在屋里不安地看着窗外,隐约觉察到有什么坏事正在发生。面对这阿鼻地狱般的光景,就连加工车间里最资深的老手也要为之动容。过去编织的肥皂泡一个个破灭了。国库的存粮并没有他们承诺得那么宽裕。粮仓见底以后,一次次令人失望的赈灾行动让民众的叛逆情绪四处蔓延。远方再次传来了食人生番的传闻,暴动几乎在所难免。虽然皇帝已经罢免甚至处决了办事不利的官员,但是磨刀声和窃窃私语声却依然再次响彻林间。同样的声音也在皇帝的城堡里回荡,蚕食着老皇帝的理智。暴乱开始那天,卫兵找到他时,他仍然在塔楼里手舞足蹈,踩着神婆的舞步,唱着神婆的歌。他们拖他去避难,一路上,他还念叨起小贝和他妹妹的名字。半个月以后,当暴民冲破甲士阵列,闯进皇宫时,看到的皇帝也是这副模样。他们拉他去刑场,来到预先挖好的大坑前,由革命领袖面朝大众宣读他的罪过。听闻宣讲人的慷慨陈词,皇帝仿佛一瞬间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他忽然清醒了,两眼圆瞪,挣扎着,大喊大叫起来。“尽人事,听天命!”他叫喊着,喊到声嘶力竭,直到人们堵住他的嘴巴。闹剧虽短,却救了皇帝的命。处刑人将他推进大坑,正要填土,预先准备的土方却忽然塌了。大地剧烈的摇颤把所有人都掀翻在地,而等他们再爬起来,枯死的建木竟然再度迸发了生机。皇帝躺在坑中放声大笑,不久后,又开始尖叫。头顶,枯死的树枝开始裂变,分裂成密密麻麻的细枝。一些细小嫩枝探到皇帝的鼻尖前,搔得他又笑又叫又喷嚏连连。是手指,数百万,数千万的手指。建木的主干也开始扭曲变形,脱去干枯的鳞片与角质,现出趾、足、胫、膝、股、腰、臀、腹、肋、乳、肩、颈和头颅,直到少女原原本本的姿态顶天立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接着,戳进皇帝鼻孔的指节“啪——”地一声断了,生出指节的木质手掌也碎成一地渣滓。山一样的少女仅以全貌示众了片刻,便轰然崩塌,残肢断臂在触地前尘归尘,土归土,扬起冲天灰烬,掠过曾经受她荫蔽的都城,随风涌向云际,与天地融为一体。异变结束。皇帝钻出尘埃,人们也钻出尘埃,木然地看向彼此。经过尘埃的洗礼,他们一时间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是怔怔地举目四顾,等待事情进一步演变。在尘埃中,人们刨出一具严重变形的骷髅。骷髅现世时,镶嵌在一块尚未完全化为尘埃的木头里,怀里还搂着喷壶、铁铲和木偶女孩。皇帝不知道此事,他已经脱去旧日身份,和所有人一样,正在茫然寻找自己在更新世的位置。有什么绊倒了他,是一截露出地面的树桩。他翻过身,端详起那桩子,忽然凑近前去,接着露出幸福的笑容。旁边的人随他看向树桩,他们的脸上也纷纷焕发出类似的荣光。枯木上隐约有一星绿意,定睛一看,是一颗细小的嫩芽。他们打量着这生命的象征,与此同时,更多嫩芽开始从缆线般的树根中探出脑袋。人们耐心等待着,没等多久,新的森林便成型了,起初是柳、杨、枫、桦、柏,接着是苹果、蜜桃、香梨、脐橙、柚子、西瓜、草莓、柿子、葡萄,以及数不清的花草、灌木、乔木、真菌、苔藓、地衣……人们守着点点新绿,慢慢意识到它们和昔日林木的区别。皇帝也醒悟了。他弯下腰,用手指刨土,刨到指甲迸裂,却只挖开了浅浅一层浮灰,灰尘下方是密密麻麻的细小根须,彼此缠绵交织,严丝合缝。在最后一次蜕变中,建木的根系取代了地层,变成了新的土壤。它的筛管和导管捕获了逃向地层深处的水,唤醒了沉睡的养料,将水循环和物质循环转移到根系内部。从此,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灵都将自根须而生,或臣服于根须。神婆、兄长、姐姐、小贝,前人所做的一切,不论意欲为何,最终指向的,都是这个结果。他走向那具怀抱少女偶像的枯骨。枯骨咧开嘴巴,面朝苍天,露出灿烂的笑容。皇帝也笑了。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他一边絮絮叨叨,一边俯身抚摸小贝的残骸,然后站起身来,走向远方。绿油油的草叶没过了他的脚掌,在他的四周,雏菊和紫丁香正在如喷泉般四处飞溅。他走了很久很久,走出盆地,走过山峦,走进已经变成大草原的平坦旷野。一滴水忽然打在了他的头顶,他抬起头,用大张的双眼接住了更多的水滴,直到电闪雷鸣,风狂雨骤。雨下得越来越大,又渐渐安息。他赤脚踏过丝绒般的土地,任由柔软湿润的根须爱抚他的脚掌。在他身后,不知名的野草吐出一对子叶,探头探脑地看向这个世界。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科普中国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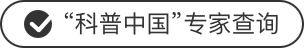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