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种内变异是指同种生物不同个体间的表型或遗传差异。种内变异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类群中,是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开篇就详细讨论生物在家养和自然状态下的变异,反复强调种内变异和种间变异是连续变化的。种内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原材料,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育种学家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种内变异的人工选择来创造具有某种特性的动植物品种。在群体遗传学和数量遗传学 中,种内变异是最基本的概念,是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此外,在保护生物学中,种内遗传变异的丧失被认为是某些野生物种濒危的重要原因。
种内变异的来源和结构.从发育和遗传机制来看,种内变异主要通过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tion)和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2 种机制产生。遗传变异即由基因型决定的可遗传的性状变异,在群体水平可称之为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随着种群内基因型数量的增加,生物性状的个体间差异也会变得更加明显。遗传变异是种内变异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型可塑性使得同一个基因型对不同环境应答而产生不同表型,这种应答让基因型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响应。尽管环境诱导的表型变异本身不一定能被后代继承,但是这种 “应变能力”常常是可以遗传的,是生物适应环境异质性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种内变异常常是基因型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植物尤其是克隆植物中,表型可塑性是种内变异的一个重要来源。从组织层次上来看,种内变异至少可以分为3个层次:①种群水平的变异,即同一个物种的不同种群的性状特征的变异。这种变异可能是由各种群间的遗传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源于各种群对不同环境条件的可塑性响应。②种群内个体间的变异,即一个种群内不同个体间的性状特征的差异。种群内的变异可能由不同个体的基因型差异或个体所处的微环境造成的表型可塑性导致的。③个体内的变异,即性状在个体内部 (例如植物的不同构件)的时空变化。这种变异可能是由空间环境异质性(例如树冠的阳面和阴面)、物候变化、季节性气候变化或者个体发育漂变(ontogenetic drift)造成的;个体内部变异还可能受到个体成长历史的影响,如个体当前出现的某个性状特征可能与此前经历过的疾病或干扰有关。
种内变异的类型用分类学和遗传学方法对种内变异的研究表明:种的广义多型性包括所有的分化类型。种内以及各个群体内的差异是不连续时,就把不连续的型式(根椐一个性状或根据综合性状)提到重要地位上;若是连续性时(渐变的),各个型式逐渐变得很难分开。种的分化程度是不相同的。
树木种内的分类以及变异的分级
植物种内变异出现的分类方式,涉及到性状的变异类型,直到当前,树木上仍保持着按果实、针叶的颜色、叶片开裂程度、分枝习性等各种方式命名的原则。
马马也夫把树木种内变异,分为种内变异和内生变异两个类型。种内变异划分为个体的、性别的、年代的(季节的和每年的)、生态的、地理的、杂种基因的、内生的若干个类型。
**个体变异,**主要是探讨种范围内,基因型分化出现的个体。在异交(随机交配)、突变过程和生态环境固定性变化的作用下,树木带有细小的和很大的偏差。但是,不同属的暂时性饰变是其必然的成份。由此吋见,这是个体变异的主要遗传和具体生态条件之间出现的“妥协”。
性别变异,表现 在有不同性别的生活着的群体类型中。这种变异型式,在有雌雄异株的种的树木,有这个或另一个性别的生殖器官时,最容易分辩出来。但是在森林树种的种内,雌雄异株的树种(杨、柳、五味子、沙棘、桧等)是不多的,绝大多的种,包括针叶树种在内,则属于雌雄同株的单性生殖器官。
年代变异(时间的)包括年代的(个体发育)和季节性变异。随着多年生树木的生长发育,它们的一些性状和性质,受到一系列转化作用的锻练。多年生植物的年代变异,与年周期—一定发育阶段的重复性—季节性遗传有关。对多年生乔木树种年代变异研究时,最大的困难在于有价值的经济性状,要经过栽培几十年以后才会表现出来。
生态变异是周围外界环境的一定因素对植物影响的反映。碱土区的栎树、石灰质沉积物的沼泽地上的松树,坡积物上的榆树和松树等,则是乔木树种生态变化的例子。什马里古逊指出,饰变的固定是通过无论是后备固有的;或实现了饰变适应而占据一定范围的新的饰变,在这种情况下,有价值性状的适应,以及该种在新的条件下存在的时间,即种子世代数,是决定性因素。
地理变异,是种在自然分布区内沿纬度和经度方向分化的结果。这种变异类型是在形成地理小种或气候型时出现的。地理变异的遗传稳定性是良妤的。这种性状,像开花期、光周期现象、耐寒性以及在其它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埋指示性,并能更好地遗传给后代。至于存在的长日照以及短日照,则决定于生长的地点。
杂种基因变异,主要注意到种的分布区边界处,不同种的地区的种间天然杂交;同时在一个种的群体内,也观察到极大的掺杂着其它种的性状。杂神基因变异是在长期有隔 离的分布区边界,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地方产生的。无论地质学因素,或者人类活动,都能引起破坏。冰川后期,使欧洲大陆上的乔木树阼分散开来,可作为地质作用的例证。遇到使种隔离的这些地带,种间杂种呈群集型式。例如,苏联欧洲部分的东部和东北部的芬兰云杉就是欧洲心杉和西伯利亚云杉的杂种。西伯利亚东部广大地带,散布着契肯夫落叶松,是西伯里亚落叶松和兴安落叶松的杂种。
**内生基因变异,**是单株范围内器官(叶,花,果,种子,枝条,根等)的变异。营养器官的数量性状 (叶、枝条等年増长的大小)具有极大的节律性变异。1
种内变异的测度种内变异可能涉及生物性状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基因型水平的等位基因、DNA序列等遗传变异,也包括表型水平的形态、发育、生理、生活史等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功能性状变异。根据生物性状的数学特征,又可以分为质量性状(qualitative character)和数量性状(quantitative character)两大类。质量性状变异常常表现为不连续的离散值(如孟德尔豌豆实验选取的性状:红花VS白花;圆粒VS皱粒;高茎VS矮茎),而数量性状的变异则常常是连续的数值(如叶片面积)。在基因型或基因组层面,大多数性状属于离散性状,种内变异主要包括丰富度(rich-ness))和均匀度 (evenness))两个方面。常用的测度指标包括:等位基因多样性(allelic diversity)、等位基因丰富度(allelic richness)、基因型丰富度(geno-typic richness) 、各种多样性指数(如 Simpson 指数、Shannon指数等)、杂合度(heterozygosity)、多态位点百分率(percentage of polymorphic loci )、突变多样性和有效种群大小(mutational diversity and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核苷酸多态性 (nucleotidediversity)等。在功能性状层面,质量性状变异同样可以利用各种多样性指数(例如前面提到的Simp-son 指数等)来估计,而数量性状变异一般采用平均值和方差(或变异系数)等统计参数来进行测度。在数量遗传学中,表型的方差(Vp)常常被分解为遗传方差(Ve)和环境方差(VE))2部分,其中遗传方差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加性遗传方差(Va)和显性遗传方差(VD )等不同的方差成分,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遗传力(heritability)。然而这种方差剖分( variance partition)方法一般适用于遗传谱系已知(例如北卡罗来纳设计Ⅰ或Ⅱ)或环境条件已知的实验群体(例如同质园条件下的种群)。在大多数自然种群中,个体间的遗传关系是未知的,环境又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很难进行这种定量剖分。在生态学研究中,度量种内变异和种间变异的相对大小可能更有意义(例如上文提到的T参数)。在遗传学和生态学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针对不同层面和类型的种内变异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方法,当前还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标可以取代其他指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测度指标是对种内变异不同方面或特性(例如丰富度和均匀度)的度量,由于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利用不同指标测度和比较种内变异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例如,基于基因型的指标(如基因型丰富度)和基于基因组的指标(如杂合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当种群中基因型数量增加时,基因组的杂合度未必会增加,与此相似,对应的功能性状的遗传方差也未必会随之增加。 生态学研究中常常会出现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至少一部分可能与采用不同的指标有关,这样的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直接比较的。因此,研究者在解释实验结果、推导实验结论、构建理论框架时,要特别注意测度指标的影响。
种内变异的生态效应研究当前,有关种内变异的生态效应的研究主要采用3类方法:①针对大尺度生态格局,以观察为主的方法。②在小尺度可控条件下进行的操纵性实验;③利用数学模拟等手段进行的理论模型方法。基于观察的方法可以真实地揭示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种内变异的数量和结构,但很难直接证实这些种内变异与其他生态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另一方面,基于受控实验或理论模型的方法可以清楚地揭示种内变异(如基因型丰富度)的生态效应,但常常因为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实施,同时其研究结果不一定能直接推广到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受控实验为例,当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是直接操控基因型丰富度,在控制条件下构建具有不同基因型数量的人工种群,考察不同多样性梯度下种群的各种表现。这种实验设计的隐含假设是:基因型之间存在功能性状的显著差异,功能性状的种内变异水平会随着基因型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如前所述,基因型数量与功能性状变异、种群遗传方差等指标之间未必存在正相关。然而,功能性状的加性遗传方差才是影响适应性进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即使研究者发现种群生产力随着基因型数量增加而提高,也不能肯定这种效应是否会导致生态—进化过程之间的动态互作。同时,有时研究者为了确保基因型之间存在显著功能性状差异,利用不同地理来源的基因型来构建人工种群。这种处理虽然可以确保功能性状变异水平会随着基因型数目增加而提高,但是可能会与自然种群中种内变异的实际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可能无法解释自然界中真实发生的生态过程。因此,这3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也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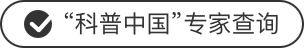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