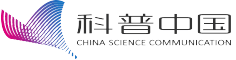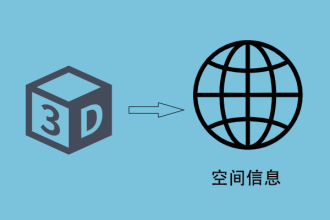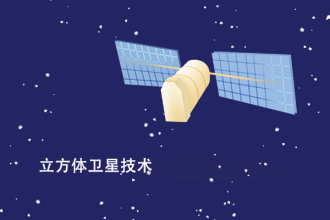深海研究老将汪品先:60岁初上阵 活着回来就算赢中国科学报 2018-06-22 作者:王庆 |

“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汪品先开玩笑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那是1959年的夏天,一辆从高加索山上下来的卡车底朝天翻倒在黑海岸边,被压在底下的莫斯科大学地质队员里,有个叫汪品先的中国学生。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前面等待着他的,是要比翻车更糟糕的“折腾”。
1960年回国前后的“重点批判”,“困难时期”的政治运动,汪品先遭遇的是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文革”期间,他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几乎绝望地以为将来的生存环境“就那样了”。
但是这位推动中国深海研究的先行者、国际大洋钻探首位中国首席科学家,更没想到会在该退休的年龄迎来学术上的黄金期。对于汪品先来说,“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他开玩笑说:“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因为他自认为“有点分量”的工作,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做的。“到了晚年,才挖到了深海研究的学术富矿。”
《老人与海》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读者,而汪品先对于大海,不是征服,不是挑战,而是永恒的探究和深情的守望。
“中国觉醒了”
如果说距离产生美,神秘激发兴趣的话,那么“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则对汪品先散发着持久的迷人魅力。
人类进入深海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海洋平均有3700米深。由于隔了巨厚的水层,人类对深海海底地形的了解,还赶不上月球表面,甚至赶不上火星。
正所谓“山高不如水深”——陆地最高的珠穆朗玛峰8800多米,而海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却有11000米。到目前为止,有3000多人登顶珠峰,400多人进入太空,12个人登上月球,但是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至今只有3人。
自古以来,海洋开发无非是“渔盐之利,舟楫之便”,都是从外部利用海洋。当代的趋势,却是进入海洋内部,深入到海底去开发。
现在全世界开采的石油1/3以上来自海底,其经济价值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世界海洋经济产值。
各国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重视甚至争夺日益激烈。要想获取,必须先搞清楚深海底部“有什么,怎么办”。汪品先探究和守望的,正是这片蕴藏着无尽宝藏的战略领域。
但是直到近几年,深海研究在我国才提上日程。为海洋科学呼吁20多年的汪品先,现在才感到如鱼得水,“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
其实,学古生物学出身的汪品先本来对海洋的了解也很有限,真正让他大开眼界,看到国际海洋科学前沿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的考察和进修。
1978年,汪品先随团访问法国和美国。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很多认知需要重新建立。两个月在十多个城市学术机构的访问,以及接下来获得“洪堡奖学金”在德国一年半的研究,使他懂得了什么是当代科学,特别是海洋深处的研究。“如果说,苏联的5年学习获得的是扎实的基础,那么从德国学到的则是活跃的学术思想。”
而那段时期,国内在海洋研究的很多领域还处于落后和空白的状态。汪品先和同事们就是依靠简陋的设备,建立起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他们住的宿舍以前是个肝炎病房,工作的实验室是个蚊蝇成群的废旧车间,用来研究微体化石的是两个对不上焦的显微镜。
尽管如此,但汪品先和同事们还是在1980年完成出版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文集,后来又出了英文版。这本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十几个国际学报纷纷报道。“中国觉醒了。”法国一本学术期刊在对该文集的评论开头这样写道。
“能活着回来就算赢”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落后,正是从海洋开始的。
1840 年的鸦片战争、1894 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与八国联军的战役,都是首先败在海上。汪品先则希望通过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为国家重新在海洋找回自信的道路上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1991年汪品先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够分量的”机会依然没有到来。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汪品先终于迎来了中国参与“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的机会。
而这种深海游戏,只有在经济和科技上都具备相当实力的国家才玩得起——20世纪地球科学规模最大的深海钻探计划,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为由10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每个耗资逾700万美元的钻探航次,由国际专家组根据各成员国科学家提供的建议书投票产生。
1995年,汪品先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建议书,1997年,该建议书位列全球排序第一,被正式列为ODP184航次。而有的建议书提了十多年都未被采纳。
1999年,该航次在南海实施,汪品先是首席科学家。“走的时候,我跟老伴说,能活着回来就算赢。”这位当时已年过六旬的科学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我连大洋钻探的小兵都没当过,现在一下子要当首席,压力很大。”
海上工作本来就有风险,何况深海海底的钻探。海盗警报还没过去,又遇到了雷达失灵……不过对于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汪品先而言,最大的压力来自工作本身。在海上工作的两个月里,汪品先的生物钟彻底被打乱了,每天只敢睡一会儿。“大洋钻探是需要砸钱进去的,每天的成本超过10万美元,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将非常巨大。”
一番劈风破浪之后,汪品先终于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不仅实现了中国海区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南海的南沙和东沙深水区6个站位钻井17口,取得高质量的连续岩芯5500米,还为南海演变和东亚古气候研究取得了3200万年前的深海纪录。
大洋钻探是国际合作项目,钻探船是美国的,船长也是当年打过越战的美国老兵。汪品先至今记得在南沙海域,当第一口井开钻的时候,船长下令升起中国国旗时的场景。“那个意义,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钟情南海
在深海研究中,汪品先对南海情有独钟。
法国的古海洋学家卡罗·拉伊曾描述,中国南海中可能会有地球上最迷人的地质纪录。
在汪品先看来,要从根子上了解边缘海的资源和环境,最好是解剖一只“麻雀”。南海作为边缘海,正好是只“五脏俱全”的麻雀。
他进一步解释道,与大西洋相比,南海海域规模小、年龄小,便于掌握深部演变的全过程;与太平洋相比,南海沉积速率和碳酸盐含量高,正好弥补西太平洋的不足。
经过汪品先和学界同道的共同呼吁,“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立项,是我国海洋领域第一个大型基础研究计划,预计执行期为8年(2011~2018年),总经费至少1.5亿元。
这项计划的目标在“深部”,采用一系列新技术探测海盆,揭示南海的深海过程和演变历史,再造边缘海的“生命史”,争取为国际边缘海研究树立典范。
作为指导专家组组长的汪品先介绍说,南海深部计划的立项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和研讨,主线是解剖南海这只“麻雀”的生命史, 包括三大方面内容:从海底扩张到板块俯冲的构造演化,是这只麻雀的“骨架”;深海沉积过程和盆地充填,是它的“肉”;深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是它的“血”。
目前,全国四十多个实验室、三百多位科学家,正在从不同学科共同探索南海的深部。将近3年来他们完成了几十个航次和航段,正向纵深推进。南海的第二次大洋钻探,将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前从香港起航,钻探南海的大洋地壳,两位首席和多位航行科学家都是“南海深部计划”的研究骨干。我国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也已经在今年6月下潜南海北部探索冷泉和海山……
布局海底观测网
在完成和推动上述深海科研项目后,如今在汪品先推动深海科技的目标清单中,列在第一项的便是建立海底观测网。
据他介绍,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部不断扩展视野的历史。假如把地面与海面看作地球科学的第一个观测平台,把空中的遥测遥感看作第二个观测平台,那么在海底建立的将是第三个观测平台。
“人类历来习惯从海洋外面研究海洋,而海底观测网是在海底建造气象台、实验室,从海洋内部研究海洋。”汪品先说,如果在海底布设观测网,用光电缆供应能量并传输信息,就可以长期连续进行原位观测,随时提供实时信息,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海洋的途径,所有相关的研究课题都会为之一新。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人类和海洋关系的改变。2009年,加拿大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海底观测网,2014年美国将建成更大的观测系统。美国人说,若干年以后,人们在家通过电视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海底火山爆发的壮观场景。
在这场被视为海洋科学新革命的进程中,汪品先希望中国不再“迟到”。“只有尽早介入,才能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取得话语权。”
多年来,汪品先是呼吁者,也是践行者,为推动建立海底观测系统而奔忙。
《国际海底观测系统调查研究报告》这个由他牵头完成的内部报告,经多次修改于2011年形成了最终版本——《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009年,在汪品先领衔下,中国第一个海底综合观测试验系统——东海海底观测小衢山试验站建成并投入运行。2011年,中国的深海观测装置在美国加州900米水深的试验站对接成功。
同年,由汪品先所在的同济大学牵头,提出在我国东海和南海建设国家海底观测系统。2013年,这项建议已经正式列入“十二五”国家大科学工程。
采访手记
赤子心 家国情 无止境
除去出差以外,办公室是汪先生的大半个家。
两次采访中的一次是在周六晚上八点多,平日的那个时候本是他的工作时间。“不过我一般11点之前会到家,不然老伴儿会生我气。”他笑着解释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算“太长”。
为了避免被外界过多打扰,除了叫车的时候,他从不用手机。
1936年出生的汪品先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赤诚和信仰。
家国情怀和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经常从专业领域考虑国家海洋战略的他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时期,他觉得国家困难,从苏联回来坚持不用“糕饼票”之类的标证,后来犯了浮肿。
从上海“十里洋场”长大的他,在念书的岁月里总觉得有“原罪”,真心诚意地想批判掉“个人主义”。 他甚至曾深深地怀疑和批判过自己的“自私”——1959年车祸醒来后,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还活着”,而不是先想到他人。
后来的经历,尤其是“文革”的洗礼,才让他反思当年接受的教育是否正确。
在国外的考察和进修期间,他慢慢领悟到科学的创造需要自由的空气。从学成回国到如今接近“杖朝”之年,他也一直没有停止科学的思考和反省。
在他看来,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巨大,发展速度也令世界瞩目,但管理层面的急功近利和文化层面的沉沦,“也许使问题比成绩长得更快”。
“我们的做法偏了,总的来说,我们是拿抓工程的方法来抓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目标过于明确,过于强调物质化的结果,这样不利于形成健康的科学研究风气,也出不了真正大的成果。”汪品先不无忧虑地表示。 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强调物质为主,精神的东西就放松了,而且缺乏对历史的反思。“我总觉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完全可以冷静下来,想想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研究海洋的汪品先已经历过人生的风浪,他明知道说的不见得符合主流观点,期望中的改变也不会立刻发生。“但是如果连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那才是真的糟糕。”
责任编辑:王超
下一篇:汪品先求解深海之谜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