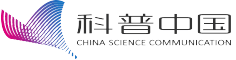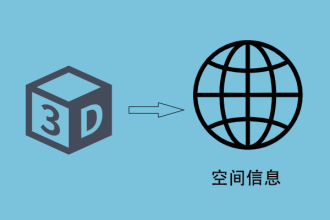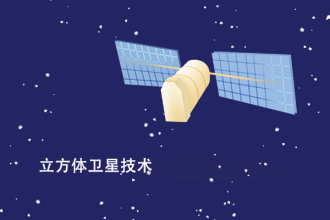【小说】旴涯——碧血烽烟(下)科普中国-科普创客空间 2017-03-16 作者:泰坦 |
作者:阿丽耶特·德·波达尔 翻译 胡绍晏
天宝站在太空港里,与家人簇拥在一起。她挽着祖母的手,而老人家正与二婶和母亲交谈,情绪激昂地抱怨着周围的一切,从漫长的等待到邻居的噪音。
她透过窗口望着军队的战舰——而叛军智船幽黑的影子也在悄无声息地逼近——她心中寻思,帮助他们撤离的船只何时才能作好准备。四周的人们脸色凝重,不停地望向显示屏,望向一动不动的队列,望向卫兵们无动于衷的脸。
前方有一顶浮轿:这很奇怪,因为浮轿只可能属于高级官员,但他们可以直接排到队列前面去。天宝拽了拽祖母的衣袖。“祖母?”
“怎么了,孩子?”祖母连头都没回。
“轿子里是谁?”
“哦。”祖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那顶轿子。黑漆外壳,金雀浮雕,拱顶上有一只展翅的仙鹤。“大概是莺女士——你应该不记得她,但她在隐居前,跟你母亲同属一家诗社。一直都是个古怪的女人。”她皱起眉头,“但我以为她有自己的智船——她出现在这儿还真奇怪。”
“莺女士?”
然而祖母已转回身继续与母亲和二婶交谈。
上方,帝国军的舰船并未移动,但天宝看到叛军智船的形状越来越清晰,它们从深维空间中冒出来,已作好发射武器的准备。他们打算……
她在事发前瞬间便预料到了——只见一团如极光般的致命光晕在空中无声地扩展,吞噬了帝国军最大的一艘舰船——那艘船一阵颤栗,仿佛蛋壳一样碎裂——然而可怕之处在于,虽然黝黑的液体泄漏出来,在天空中逐渐扩散,船体本身却依然保持着原形——阵阵颤抖,但并未散开,在如此强烈的冲击之下,生命维持系统必然已经损毁,船上的所有人一定已经死亡,或正濒临死亡,或遭受着更可怕的折磨……
在随之而来的沉默中,有人发出一声嘶喊,他的嗓音低沉震撼,于是人群陷入了疯狂。
突然间,人们朝着船坞涌去,互相挤攘,有些人被狼狈地推倒在地。天宝发现自己被挤到祖母身边,挣扎着在人群中保持站姿——一条条胳膊推搡着她,令她与家人分离,她迷失在陌生的面孔中,在人潮的拉扯下,她竭尽全力才能勉强站立与呼吸——
原本处在她视野边缘的黑影覆盖了一切。梦境中滚动的红色字体再次组成那句清晰简洁的话语。
小妹,召唤我。召唤我,终止这一切。
她悬浮在黑暗的太空中,排出的离子云拖出一道尾迹,仿佛展开的巨型扇面;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被打磨成犀利的杀戮工具——她是一件具有生命的武器,火力足以毁灭一切,足以将叛军舰队化为灰烬,足以将它们轰成碎片,就像击碎那艘帝国军舰船。她只需联络游移于群星间的自己,召唤那庞大而黑暗的另一半……
有人抓住她。她还没来得及发出惊叫,一双冰冷的手便攫住她的双肩,将她提起来。硕大的空间感连同红色的字体,以及头脑中另一个存在都一齐消失了。
她坐在黑暗中。片刻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在浮轿里,眼前约摸可辨的身影是一位老妇。
莺女士。
“孩子,”老妇说道。维持生命的管线从轿身的各个角落悬垂下来,她就像坐在一张蛛网的中心。昏暗的光线里,她脸上的皮肤如同湿润的宣纸一般苍白而透薄;她的双眼仿佛黑暗幽深的洞窟。“阿光和阿如的女儿,对吗?我是你母亲的朋友。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就像上辈子的事。”
一切安静得出奇:外面没有动静,始于船坞的暴乱变得毫无声息——当然,浮轿一定拥有最好的氛围系统,但这整体效果——那种悬浮于人工静止时空泡中的感觉——令天宝汗毛直竖。“莺女士。为什么——?”
母亲和二婶一定非常着急,她们一直告诉她不要相信陌生人。而她此刻被困在暴乱的中心,跟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人呆在一起,无法脱身——但莺女士又何必要绑架她呢?她是一名学者,一名公众人物,至少曾经是。话虽如此……天宝接通自身的线路,激活定位器——她曾向母亲保证,自己已是成人,不再需要定位器,此刻她很庆幸母亲并未听从。
老妇微微一笑,但那笑意并未企及双眼。“你宁愿呆在外头?相信我,这里要安全得多。”天宝视野的左下角有信号闪烁,那是播放视频的请求。确认请求之后,她便看到了外面的景像。
浮轿依靠斥力场漂浮于空中,在人群中辟出一条路来。天宝知道,自己在外面连片刻都支撑不住,立即就会被争抢着涌向穿梭机的人群放倒。但是……
莺女士语声不高,但语气坚定。“你刚才看起来就像一心想要被人潮踩死。”
“你不必——”
“对,”莺女士说,“你说得对。我不必救你。”
她年纪有多大?天宝心中寻思。要过多久皮肤才会变得如此苍白,双眼才会变得如此深邃,仿佛已站在生死边界的另一侧?她年迈苍老,却拒死神与门外,这是否借助于天宝祖先的智慧?
“暴乱的人群里可不适合发呆,”莺女士说,“不过以你的年纪,或许情有可原。”
就是说她没注意到天宝陷于出神状态。然而话说回来,她怎么可能知道呢?虽然她的确年长睿智,却并非全知全能。“抱歉。”天宝说。但她依然记得那广阔无垠的感觉,以及体内蓄势待发的能量。假如那是真实的,假如那不是梦境,假如她能够作出回应……
召唤我,小妹。让我们终止这一切。
天宝说:“听祖母讲——你有一艘智船——”
莺女士笑出声来,似乎真的是被逗乐了。“‘跃鲤号’吗?独占她的资源好像没有意义。她加入了协助撤退的舰队。事实上,我们正要去那儿。”
莺女士的视线聚焦在天宝身后,然后她点点头。“我会发信息给你家人,说我要帮你登船。这样应该能够减轻她们的忧虑。”
假如她们没有死于叛军的火力,假如剩余的那艘帝国军飞船能守住防线——假如,假如,假如……
浮轿轻轻摇晃,说明它又在往前挪移——朝向等待着的飞船,朝向安全之处——只不过现在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外面,剩下的那艘帝国军飞船仍试图拦截叛军智船,其外壳在震颤中凹陷皲裂。时不时会有流弹击中空港的防护罩,整个建筑都在振动,但它依然没有倒下。
然而,还能挺多久?
“我恨他们。”天宝说。
“恨谁?叛军?”莺女士眼神锐利,“朝廷跟他们一样有责任,孩子。要是硕德皇帝和百合女皇没那么懦弱,更注重军队,而不是诗词;要是那些官员没有怂恿他们,总是胡扯什么专注于德行是唯一能保障帝国安泰的方法……”
她竟如此随意地评判女皇——但二婶和母亲也一样。“我希望……”天宝知道,自己的话听起来非常幼稚,就像蹒跚学步的幼儿要求未获满足。“我希望有人能够阻挡叛军。一劳永逸地歼灭他们。”
莺女士不露声色,但摇了摇头。“要小心,孩子。”
期盼和平难道错了吗?这个养尊处优的老妇什么都不明白,她不必在人群中挣扎,不必心怀恐惧地活着,她脑中的家族历史已经丢失——
“杀戮是很简单,”莺女士说,“但永远无法阻止残酷的战争。”
“但那是个开始。”天宝辩解道。
“也许吧,”莺女士说。她摇了摇头,“帝国必须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才能阻止他们,然而我们目前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失败的种子恐怕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埋下,而且——”
她永远未能说完这句话。天宝没看见什么,但防护罩被击中,其能量消耗殆尽,仿佛湿洗衣物中的水分被生生绞干。在她们四周,网状的裂纹在空港的立柱与玻璃窗之间蔓延。天宝想要说,小心,但离她们最近的墙壁一阵颤栗,连带着天花板的碎块一起塌落下来。她的后脑勺被砸中,随着一阵揪心的剧痛,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
#
“朱凤号”在隐匿期间,仅有一名船员,她是锦绣卫队的军官——虽然并非血亲,却是一位结义姐妹,在船上已有数十年,绝不愿离弃岗位。
这名军官命运如何并无资料记载。作为一名人类,又不曾经过生物改造,她多半已经老死,而没有负担的智船则能继续生存下去——所有智船皆是如此。
没有负担并不意味着没有悲哀与孤独。在随后的数百年里,有些人声称在幻像中看见这艘飞船,听见她召唤他们,或者梦见战场——有过去的,也有现时的——然后目睹她以残酷的手段终止战斗。这些人之间并无关联,没有共同的祖先,时间和空间上也相隔甚远。但也许那艘智船依靠其他东西来辨识人选:某个灵魂,剥离了脆弱的肉体,一次次重生,直到一切都不再有差错。
#
天宝醒过来,到处是尘埃与砂砾——呛得她弯腰趴在地上一阵阵咳嗽,肺感觉就像被绞干了似的。最后,她颤抖着站起身,看到浮轿的残骸半埋在碎石底下,若干被截断的管线在昏暗的光线中无力地摇摆——稍远处,混乱的人群仍然挣扎着朝飞船涌去。她以为墙会崩塌,然而尽管从上至下布满巨大的裂隙,它却依然不倒。虽然并非贴切的类比,但这让她想起父亲视如珍宝的青瓷杯盏,其表面也布满网状纹隙,却并不碎裂,简直像是奇迹。
她的四周到处散落着天花板的碎块——还有其他东西,她避免直视——许多人躺在地上,有的静止不动,有的阵阵抽搐,还有的半埋在碎石堆下不停地呻吟——四肢弯折成异常的角度,滴血的伤口中露出白骨。有人肚破肠流,有人在痛苦中费力地喘息……
如今是死亡的年代,她必须坚强。
在她视野边缘悬浮着梦中的红色字符,呈半透明状,隐约可见——类似《靛山之战》的暂停画面,但那游戏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她依稀感觉到,某种巨大的存在正从远处注视着自己。
“莺女士?母亲?二婶?”她的定位仪仍在运作,但似乎没能探测到她们的信号——或许是空港网络的问题,时断时续,就像濒死的心脏。不过这反正也没什么意义,有谁指望在如此攻击之下,网络仍能保持稳定呢。
头顶的天空里,有个黑沉沉的影子——并非帝国军飞船,因此只可能是那艘智船。它的舱门敞开着,从中冒出数十艘小船,缓缓降落:前来收拾残局的叛军。
她必须行动起来。
她挺直身子,脖子和双臂一阵疼痛,犹如刀割,但她逼迫自己半走半爬往前挪移,直到找到莺女士。
老妇人躺在碎石堆里,瞪视着空港残破的穹顶。天宝久久地注视着她,期盼她还活着。但没人可能在下半身被压烂的情况下依然存活,况且还有那么多液体和鲜血从破损的管子里漏出来。“抱歉。”她说道,但那不是她的错,从来就不是她的错。头顶上,那些小船仍在缓缓沉降,仿佛刽子手的刀刃。没时间了。到处都不安全。没有正义,没有公平。战争和恐惧无法终止,她头脑和胸口中那种不适的感觉也难以消除。
她的耳中一声鸣响,盖过了远处惊恐的人群所发出的噪音——她意识到那是定位仪,它显示了一个箭头,标示出与其余家人会合的路线。假如她们没有像莺女士那样死去,假如还有希望……
她努力站起身——跌跌撞撞按照指示的方向前进——左右左一步一移绕过浮轿绕过死尸绕过探出手爪拉拽她的伤者——这是死亡年代,她必须坚强必须坚强……
她找到了祖母、母亲和二婶,她们站在原先用来维持队伍秩序的挡板边——那些挡板跟周围的一切一样蒙着一层泥尘。母亲没有跟她打招呼,也没有流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只是点点头,仿佛一切如常,然后她说:“我们得赶紧走。”
“太迟了。”二婶一边说,一边凝神望向天空。
天宝试图交谈,她想要讲莺女士的事,但一个字也说不出。
母亲的眼睛短暂地往上翻起,她在连接网络。“‘跃鲤号’,”她说,“它的穿梭机群停在候机楼的另一端,那里人比较少。来吧。”
快走快走快走——天宝感觉一切都变成了黏滞的沥青。她麻木地跟着二婶和母亲从人堆里挤过去,来到一条过道里,此处跟其他地方拥挤的人潮相比,几乎像是废弃了一样。“这边走。”母亲说。
在她们蹒跚地走入过道之前,天宝短暂地回头瞥了一眼,看见第一波叛军穿梭机已在稍远处着陆,士兵蜂拥而出,他们身穿黄色制服,头戴毫无装饰的盔帽。
她仿佛又回到梦里,只不过她的梦境从未如此紧迫——视野边缘的红字不停闪烁,无论她如何努力迫使它们消失也不管用。
母亲说得对,她们必须不断前进——她们走出过廊,进入一条宽阔的主干道,里面到处散落着废墟。她们跟随稀疏的人流往前走,希望穿梭机仍在等候,希望莺女士死后,智船仍会回应他们。此刻,其他人也加入她们的行列,其中一名士兵背着一个受伤的女人——没有互相介绍与致意,但大家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命运都牵系在一起。让他们坚持下去的并非希望,而纯粹是固执,一步步往前跨,一次次呼吸,害怕落后于他人,害怕拖了众人的后退,害怕把一切搞砸。
前方的玻璃窗外,可以看到一群穿梭机,距离如此之近,令人心焦难熬。“这边走,”二婶说。接着,她们看见前方有穿黄色制服的士兵堵在主干道上——另有士兵挡住各处过廊,在诡异的沉默中将人们驱离穿梭机的方向。
母亲明显丧失了信心。“没事的,”她说,但听她的语气就是在说谎。“他们只是核查一下身份,然后就会让我们——
然而,跟他们在一起的那名士兵变得惊慌失措——他背负着伤者转身飞奔——紧接着,在滞塞的沉默中,天宝听见武器上膛的咔嗒声。
“不要!”母亲尖声道。天宝仿佛是在梦里,她看见母亲走到穿黄制服的士兵跟前,就像在集市里闲逛那样不假思索——她想要尖叫,却发不出声。武器击中了目标,母亲瘫软下去,看不见鲜血,她的尸体如此之小,几乎无法想象她曾经有过生命。
最后,二婶也作出了行动,她满脸怒容——并非朝着母亲或那名士兵,而是面对叛军部队。“你们竟敢——”
又是武器上膛的声音。
不要。
不要。不要。
一切都变成红色:梦中的字符再次出现在她眼前,话语声也在脑中响起。
小妹。
天宝一边流泪,一边让思维向着群星间的真空延展,召唤那艘飞船。
#
当一个叫天宝的孩子出生在第六行星时,伴有特殊征兆——屋里充斥着机油的气味,墙上泛出若隐若现的七彩字符,属于某种远古失落的语言。若不是因为母亲意外地大量出血,助产士一边拼命忙着止血,一边还要安抚焦虑的父亲,她或许就能注意到那些异象。当新生儿颤抖着呼入第一口气时,助产士若是望向她的眼睛,便会看到另一个预示未来的征兆:硕大的瞳孔中闪烁着一丝深邃的金属光泽,整个眼睛里仿佛盛满了熔化的钢铁。
#
她古老而巨硕,令人畏惧;她展开的翅翼可以覆盖整个行星,并且闪烁着晶莹的虹彩,如同产自深海的珍珠;她引擎尾迹的颜色既像翡翠,又像精致的青瓷——她经过哪里,便将杀戮带到哪里。
她消灭了等候在战场外围的舰队,又夷平了那颗小卫星的地表,对于困在卫星上的人们发出的声声嘶喊却不予理会;她下降至行星大气层顶端,将轨道上的两艘智船化为灰烬,也摧毁了那艘依然在竭力防御智船的弱小飞船;卫兵们仍在殿堂里与刚着陆的入侵部队交战,总督在自己的套房内凝视着地表战略图,盘算如何尽量减少损失,这些地方也都被她尽数炸毁。空港里聚集着大量人群,她扔下一枚枚离子炸弹,直到那里不再有生命迹象;直到每一艘穿梭机都炸裂开来或停止移动。
然后是一片寂静,不再有争斗冲突,只剩下平和安宁。
接着,她又变回了天宝,站在空港的废墟内,站在她召唤来的巨型飞船所投下的阴影里。
这里什么都没剩下,只有尘埃与尸体——如此之多,犹如一片海洋,有黄制服,有黑制服,平民,帝国军和叛军全都混杂在一起,鲜血在开裂的地板上汇聚成潭。围绕在她四周的,有她母亲,还有那个士兵和受伤的女人,以及射杀母亲的那几名叛军成员——二婶和祖母也一动不动地躺在母亲身边,苍白而毫无血色。他们不知是死于智船的武器还是叛军的武器,但天宝发现自己站在死者中间,是唯一活着的人。
唯一活着的人——不可能——不可能——
小妹。智船的话音如海洋般深沉。我已应你所求而来,将一切终止。
这不是她想要的——这一切的一切——
然而,她记起莺女士的声音,记起她揶揄的话语。要小心,孩子。要小心。
我带来了和平,终止了争斗。这难道不是帝国所期望的吗?
不。不。
随我来吧,小妹。让我们终止这场战争。
一场大胜,天宝一边想,一边环抱住自己。她同时感到灼热与寒冷,血肉包裹的骨髓里透出一阵凉意,胸口隐约泛起悲哀。每个人都想要一场对叛军的大胜仗,以期永远阻止他们前进,告诉他们帝国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让他们为每一颗行星付出昂贵的代价。
她满足了大家的愿望。她和那艘智船,完全满足了大家的愿望。
来吧。我们只剩下彼此,那艘船说道,但这是个苦涩的事实。行星上什么都没剩下——没有一个活口——进入星系的叛军部队也都连人带装备一起被消灭,只有损毁的舰船在空旷的太空里漂泊。
来吧,小妹。
她接受了——不然她还能去哪里,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是有意义的?
#
在古代,朱红色的凤凰象征着和平与富裕,也象征着令国土繁荣兴旺的贤明君主。
在战争年代依然是如此。如若不问和平如何获取,繁荣代价几何——一艘智船与一名儿童抹除了许多用数字编号的星球,以血腥屠杀终止战斗,将死亡一视同仁地赐予叛军与帝国;任何人想要拥有动用武器的特权,都将付出高昂代价。
同时,内圈行星上开始了痛苦的重建工作——从战争的灰烬里建起宝塔,公堂与店屋,除夕的香囊悬挂在依然布满尘埃与废墟的街衢上,以向先祖祈求更美好的未来,祈求长寿与幸运,祈求子嗣如空中的繁星一般众多。
世上并无贤德的君主,但也许——只是也许,有一种和平与繁荣可以通过鲜血的海洋来换取,只需让一名孩童来实现即可。
也许——只是也许——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在战争年代,这或许是唯一的希望。
责任编辑:科普云
上一篇:【小说】逃离末日(2)
下一篇:【小说】单程的远方(下)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信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最新文章
-
为何太阳系所有行星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
新浪科技 2021-09-29
-
我国学者揭示早期宇宙星际间重元素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报 2021-09-29
-
比“胖五”更能扛!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要来了
科技日报 2021-09-29
-
5G演进已开始,6G研究正进行
光明日报 2021-09-28
-
“早期暗能量”或让宇宙年轻10亿岁
科技日报 2021-09-28
-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新华网 2021-09-28